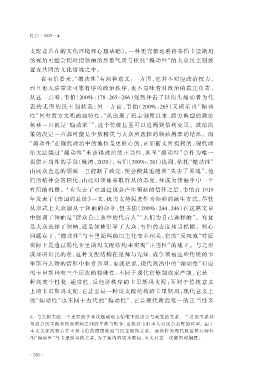Page 227 - 《社会》2025年第4期
P. 227
社会·2025·4
支配者共在的文化环境和心理基础)。 一种更完整地看待韦伯卡里斯玛
的视角可能会同时把领袖的形象气质与依托“煽动性”的大众民主制放
置在共同的文化情境之中。
在韦伯看来,“煽动性”有两种意义:一方面,它并不对应政治权力,
而且也无法带来可靠有序的政治秩序,也不意味着对政治的真正负责,
从这一点看,韦伯( 2009b:178、265-266)强烈抨击了以街头煽动者为代
表 的无 序 的民 主 制 状 态 ;另 一方 面 ,韦伯(2009b:265)又揭 示 出“煽 动
性”具有西方文明的独特性:“从出现了民主制度以来,西方典型的政治
领袖一直就是‘煽动家’”,这个传统甚至可以追溯到伯利克里。 政治决
策的决定一直都可能是少数精英与大众所选择的领袖博弈的结果。 而
“煽动性”在现代政治中的地位是更核心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现代政
治无法绕过“煽动性”来获得政治的正当性,甚至“煽动性”会作为唯一
提供正当性的手段(陈涛,2020)。 韦伯(2009b:281)提到,依托“煽动性”
由民众直选的领袖一旦控制了政党,便会使其追随者“失去了灵魂”,他
们的精神会贫困化,由此对领袖采取盲从的态度,并成为领袖手中一个
有用的机器。 6 在失去了对通过议会产生领袖的信任之后,韦伯在 1919
年发表了《帝国的总统》一文,极力支持民选作为领袖的诞生方式。 尽管
从形式上大众服从于领袖的命令,但韦伯(2009b:244、246)在这篇文章
中强调了领袖是“群众自己选举的代言人”“人们为自己选择的”。 究竟
是大众选择了领袖,还是领袖引导了大众,韦伯的态度相当模糊。 核心
问题在于,“煽动性”与卡里斯玛的民主化变革相关,它的“反权威”特征
实际上是通过弱化卡里斯玛支配结构来实现“正当性”的建立。 与之形
成显明对比的是,这种支配结构在巫师与先知、战争领袖这些传统的卡
里斯玛人物的情形中非常典型。 也就是说,现代政治中的“煽动性”对应
的卡里斯玛有三个层次的特殊性:不同于现代官僚制或家产制,它是一
种高度个性化、超常性、反经济秩序的卡里斯玛支配;不同于传统意义
上的卡里斯玛支配,它甚至是一种反支配结构的卡里斯玛;现代意义上
的“煽动性”也不同于古代的“煽动性”,它是现代政治唯一的正当性来
6. 与之相关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就是韦伯笔下的议会与政党的关系, 二者的关系涉
及议会民主制和民选领袖之间的平衡与配合,也包括韦伯本人对议会态度的转型。 由于
本文关注的核心并不是韦伯的德国政治与民主制的关系, 而是作为现代政治核心特 征
的“煽动性”与卡里斯玛的关系,为了使内容更为聚焦,本文对这一议题暂时搁置。
·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