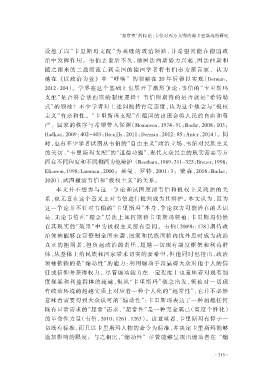Page 222 - 《社会》2025年第4期
P. 222
“超常性”的悖论:韦伯对西方文明内部卡里斯玛的研究
设想了以“卡里斯玛支 配 ”为 基 础 的 政 治领 袖 ,并 希 望 其 能 在 德 国 政
治中发挥作用。 韦伯去世后不久,德国法西斯势力兴起,因法西斯和
随之而来的二战而流亡到美国的德国学 者 将 韦伯奉为预 言 家 , 认 为
他 在 《以政治为业》 中“呼唤” 的领袖在 20 年后得以实现(Derman,
2012:204)。 学界在这个基础上也展开了激烈争论:韦伯的“卡里斯玛
支配”是否符合法西斯的制度逻辑? 韦伯所期待的是否就是“希特勒
式”的领袖? 不少学者对上述问题持肯定态度,认为这个概念与“极权
主义”有亲和性。“卡里斯玛支配”在德国的出现会将人民的自由和尊
严、 国家的秩序与希望带入深渊( Mommsen,1974:91;Baehr,2008:103;
Radkau,2009:402-403;Breuilly,2011;Derman,2012:85;Anter,2014)。 同
时,也有不少学者试图从韦伯的“自由主义”政治立场、韦伯对民族主义
的关切、“卡里斯玛支配”的“道德功能”、现代大众民主的现实需要等方
面在不同程度和不同侧面为他辩护 ( Beetham,1989:311-323;Breuer,1998;
Eliaeson,1998;Lassman,2000; 莱曼、 罗特,2001:3; 蒙 森 ,2016;Budac,
2020),试图撇清韦伯和“极权主义”的关系。
本文并不 想参 与 这 一 争 论和 试 图 厘 清韦伯 和 极 权 主 义 政 治 的 关
系,也无意在这个意义上对韦伯进行批判或为其辩护。 本文认为,因为
这一争论并不针对韦伯的“卡里斯玛”本身,争论双方可能潜在的共识
是,无论韦伯在“理念”层次上如何期待卡里斯玛领袖,卡里斯玛仍然
在其现实的“效果”中为极权主义留有空间。 韦伯(2009b:178)期待政
治领袖能够在官僚制全面来袭、国家和民族面临内忧外患时成为政治
真正的担纲者,担负起政治的责任,超越一切现有制度框架和利益群
体,从整体上给民族和国家带来切实的新希望,但他同时也指出,政治
领袖依赖的是“煽动性”的能力:利用煽动手段赢得大众对他个人的信
任或信仰并获得权力。 尽管煽动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对现有制
度框架和利益群体的超越,但从“卡里斯玛”概念出发,领袖对一切现
有政治环境的超越实质上对应着一种个人化的“超常性”,它并不必然
意味着需要得到大众认可的“煽动性”:卡里斯玛表达了一种超越任何
既有日常需求的“超常”需求,“超常性”是一种完全属己(高度个性化)
的革命性力量(韦伯,2010:1261、1263)。 这意味着,卡里斯玛有悖于一
切既有标准,而只以卡里斯玛人物的命令为标准,并决定卡里斯玛能够
施加影响的限度; 与之相比,“煽动性” 尽管能够呈现出煽动者在“煽
· 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