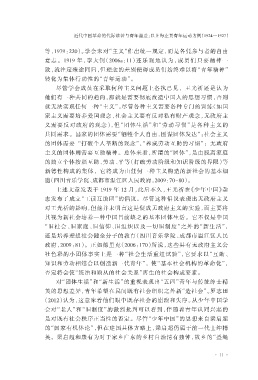Page 18 - 《社会》2025年第4期
P. 18
近代中国革命的代际继替与青年塑造:以上海左翼青年运动为例(1924—1927)
等,1979:220)。学会未对“主义”作出统一规定,而是各凭参与者的自由
意志。 1919 年,李大 钊(2006a:11)还 乐 观 地 认 为,成 员 们 只要 精 神 一
致,就注定殊途同归,但理念的差别使得成员们始终难以将“青年精神”
转化为集体行动性的“青年运动”。
尽管学会成员在采取何种主义问题上各执己见, 王光祈还是认为
他们有一种共同的趋向,那就是需要彻底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否则
就无法实现任何一种“主义”。尽管各种主义需要各种专门的训练(如国
家主义需要培养爱国观念,社会主义要有反对私有财产观念,无政府主
义需要反对政府的观念),但“团体生活”和“劳动习惯”是各种主义的
共同需求。 国家的团体需要“牺牲个人自由,图谋团体发达”;社会主义
的团体需要“打破个人垄断的观念”,“养成劳动互助的习惯”; 无政府
主义的团体则需要互助精神。 总体来看,所谓的“团体”,是由脱离家庭
的独立个体按照互助、劳动、平等(打破劳动阶级和知识阶级的界限)等
新德性构成的集体, 它将成为由任何一种主义构造的新社会的基本细
胞(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2009:70-80)。
上述文章发表于 1919 年 12 月,此后不久,王光祈在《少年中国》杂
志发布了成立“工读互助团”的倡议。 尽管这种倡议表现出无政府主义
对王光祈的影响,但他并未明言这是促成无政府主义的实验,而主要将
其视为新社会培养一种中国目前缺乏的基本团体生活。 它不仅是中国
“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之外的“新生活”,
还是培养理想社会健全分子的教育(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市温江区人民
政府,2009:81)。 正如德里克(2006:170)所说,这些具有无政府主义公
社色彩的小团体事实上是一种“社会生活重组试验”,它要求以“互助、
知识和劳动相结合以创造新一代青年”, 使“基本社会机构的革命化”,
否定将会使“统治和顺从的社会关系”再生的社会构成要素。
对“团体生活”和“新生活”的重视表现出“五四”青年与传统绅士精
英的思想差异,青年希望在民间既有社会组织之外新“造社会”。罗志田
(2012)认为,这意味着他们眼中既存社会的崩溃和失序。 从少年中国学
会对“老人”和“旧制度”的激烈批判可以看到,伴随着青年认同兴起的
是对既有社会秩序正当性的否定。 尽管“少年中国”的思想来自梁启超
的“国家有机体论”,但在建国具体方略上,梁启超仍属于前一代士绅精
英。 梁启超和康有为对于家乡广东的乡村自治情有独钟,故乡的“叠绳
·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