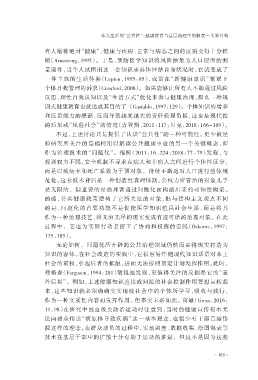Page 172 - 《社会》2025年第4期
P. 172
私人生活的“公共性”:健康教育与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关系互构
有人堪称绝对“健康”,健康与疾病、正常与病态之间的区别变得十分模
糊(Armstrong,1995)。 于是,预防医学知识将风险抽象为人口层面的测
量属性,当个人试图用这一套知识来具体评估自身状况时,它就变成了
一种主观的生活体验( Lupton,1995:85),或是在“新 健康意识 ”笼 罩 下
个体自我管理的诉求(Crawford,2006)。 如果能够让所有人不断通过风险
反思、理性自我认知以及“生活方式”优化来参与健康治理,那么一种规
训式健康教育也就达成其目的了 (Gastaldo,1997:129)。 个体知识的增多
和反思能力的提高,反而导致越来越大的责任伦理负担,这也是现代性
的后果或“风险社会”的情境(吉登斯,2011:117;贝克,2018:166-169)。
不过,上述讨论只是提供了认识“公共性”的一种可能性。 更少被经
验研究所关注的是福柯用以解读公共健康事业的另一个关键概念,即
作为治理技术的“问题化”。 福柯( 2011:16、224;2018:77-79)发现,与
规训权力不同,安全机制不寻求在病人和非病人之间进行个体性区分,
而是以致病率和死亡系数为干预对象, 持续不断地对人口进行整体规
范化。这套技术背后是一种创造性真理体制。公权力所管治的对象几乎
是无限的, 但重要的是治理者通过问题化而构造出来的可知性构架。
的确,公共健康政策建构了它所关注的对象,但与建构主义观点不同
的是,问题化的首要功能不是促使医学知识殖民社会生活,而是将其
作为一种治理技艺,将无穷无尽的现实变成有迹可循的治理对象。 在此
过程中, 它也为实际行动者留下了协商和权衡的空间(Osborne,1997:
175、185)。
无论如何, 问题化所开辟的公共治理领域仍然需要将现实打造为
知识的客体。 在社会改造的实践中,它很容易伴随现代知识话语对本土
社会的霸权,引起后者的抵触,进而无法按照预定计划发挥作用。此时,
弗格森(Ferguson,1994:281)敏锐地发现,更值得关注的反倒是它的“意
外后果”。 例如,上述健康知识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控制作用要想运转起
来,这些知识就必须确确实实地被社会中的个体所学习、吸收与践行,
作为一种实质性内容而发挥作用。 但事实未必如此。 高敏(Gross,2016:
11、98)在研究中国血吸虫防治运动时注意到,当时的健康宣传根本无
法向群众传达“病原体导致疾病”这一基本理念,也很少有干部直接传
授这样的理念。在群众动员的过程中,实地调查、数据收集、绘图制表等
技术在基层干部中的扩散十分有助于运动的推进, 但这不是因为这些
·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