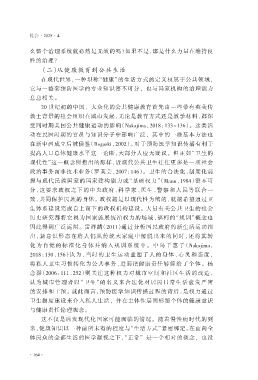Page 171 - 《社会》2025年第4期
P. 171
社会·2025·4
么整个治理系统就必然是无效的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力量在维持良
性的治理?
(二)从健康教育到公共生活
在现代世界,一种堪称“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定义权属于公共领域,
它与一整套预防医学的专业知识密不可分, 也与国家机构的治理能力
息息相关。
20 世纪初的中国, 大众化的公共健康教育首先由一些带有英美传
教士背景的社会组织在城市发起,无论是教育方式还是教学材料,都深
受同时期美国公共健康运动的影响( Nakajima,2018:133-136)。 这类活
动在民国时期的官员与知识分子中影响广泛, 其中的一些基本方法也
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借鉴( Rogaski,2002)。 对于预防医学知识传播有利于
提高人口总体健康水平这一论断,大部分人应无疑议。 但正如“卫生的
现代性”这一概念所指出的那样,近现代公共卫生往往更多是一项社会
政治事务而非技术业务(罗芙芸,2007:146)。 卫生的合法化、制度化前
提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能力或“基础权力”( Mann,1984)密不可
分,这要求政权之下的中央政府、科学家、医生、警察和人民等联合一
致,共同保护民族的身体。 政权越是以现代性为鹄的,就越希望通过卫
生体系建设完成自上而下的政权机构建设。 大量有关公共卫生的社会
历史研究都将它视为国家施展统治权力的场域,福柯的“规训”概念也
因此得到广泛运用。 雷祥麟(2011)通过分析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指
出,新意识形态在将人们从传统大家庭中解脱出来的同时,还将其转
化 为 自 觉 的 标 准 化 身 体 并 纳 入 规 训 系 统 中 。 中 岛 千 惠 子(Nakajima,
2018:130、156)认为,当 时 的卫 生 运 动 重塑 了 人 的身 体 、心 灵 和 态 度 ,
将私人卫生习惯转化为公共事务,进而把健康责任转嫁给了个体。 杨
念群(2006:111、252)则关注这种权力对城市空间和社区生活的改造,
认为城市管理者以“卫生”的名义来合法化对居民日常生活愈发严密
的安排和干预。 就此而言,预防医学知识传播过程的背后,是权力通过
卫生制度建设来介入私人生活, 并在主体性层面形塑个体的健康意识
与健康责任伦理观念。
这不仅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可能面临的情况。 随着慢性病时代的到
来,健康知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与“生活方式”紧密绑定。在面向全
体民众的全部生活的医学凝视之下,“正常” 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也没
· 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