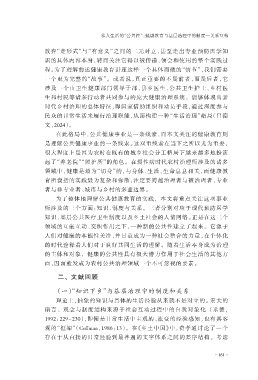Page 168 - 《社会》2025年第4期
P. 168
私人生活的“公共性”:健康教育与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关系互构
放弃“走形式”与“有意义”之间的二元对立,甚至走出专业预防医学知
识的具体内容本身,转而关注它得以被传递、领会和使用的整个实践过
程。为了理解前述健康教育讲座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情节”,我们需要
一个更为完整的“故事”。 或者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前者,而是后者,它
涉及一个由卫生健康部门领导干部、县乡医生、公共卫生护士、乡村医
生和村民等诸多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庞大健康治理系统, 能够体现出新
时代乡村治理的总体特征,即国家借助组织和动员手段,通过深度参与
民众的日常生活来履行治理职能,从而构建一种“生活治理”格局(吕德
文,2024)。
在此格局中,公共健康事业是一条线索,而本文关注的健康教育则
是理解公共健康事业的一条线索。 这双重线索在当下之所以尤为重要,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在既有的城乡社会分工格局下越来越多地扮演
起了“养老院”“照护所”的角色。 在慢性病时代农村治理所涉及的诸多
领域中,健康是最为“切身”的,与身体、生活、生命息息相关,而健康教
育所囊括的实践最为复杂和弥散,注定要跨越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专业
者与非专业者、城市与乡村的多重边界。
为了整体地理解公共健康教育的实践, 本文将重点关注这项事业
所涉及的三个方面:知识、制度与关系。 三者分别对应于现代预防医学
知识、基层公共医疗卫生制度以及乡土社会的人情网络。 正是在这三个
领域的互嵌互动、交织作用之下,一种新的公共性建立了起来。 它源于
人们对健康的本能性关注,并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整合的力量,在个体化
的时代诠释着人们对于良好共同生活的理解。 随着生活本身成为治理
的主体和对象, 健康的公共性具有极大潜力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
面,因而愈发成为农村公共治理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
二、 文献回顾
(一)“知识下乡”与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和关系
理论上,抽象的知识与具体的生活经验从来就不是对立的。 宏大的
语言、 观念与制度结构来源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自我对象化 (米德,
1992:229-230),即便是日常生活中主观的、流变的经验感知,也有其客
观的“框架”(Goffman,1986:13)。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讨论了一个
存在于从直接的日常经验到最普遍的文字体系之间的差序结构。 考虑
· 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