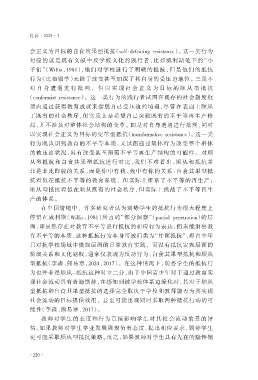Page 227 - 《社会》2025年第3期
P. 227
社会·2025·3
会正义为目标的自食其果型抵抗(self鄄defeating resistance)。 这一类行为
对应的就是既有文献中反学校文化的践行者,比如威利斯笔下的“小
子们”(Willis,1981),他们对学校进行了明确的抵抗,但是他们的抵抗
行为(比如辍学)无助于改变甚至加深了其自身的受压迫地位。 三是不
对 自 身 遭 遇 进 行 批 判 , 但 以 实 现 社 会 正 义 为 目 标 的 顺 从 型 抵 抗
( conformist resistance)。 这一类行为的践行者试图在现存的社会制度框
架内通过获得教育成就来摆脱自己受压迫的境遇,尽管在表面上顺从
了既有的社会秩序,但实质上是希望自己突破既有的不平等再生产格
局,并不涉及对整体社会结构的变革。 四是对自身遭遇进行批判,同时
以实现社会正义为目标的变革型抵抗( transformative resistance)。 这一类
行为既认识到教育的不平等本质,又试图通过集体行为改变整个群体
的被压迫状况,具有改变甚至颠覆不平等再生产结构的可能性。 对顺
从型抵抗和自食其果型抵抗进行对比,我们不难看出,顺从和抵抗并
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自食其果型抵
抗看似在抵抗不平等的教育系统, 但实际上维系了不平等的再生产;
顺从型抵抗看似在顺从既有的社会秩序,但实际上挑战了不平等再生
产的体系。
在中国情境中, 许多研究者认为弱势学生的抵抗行为很大程度上
停留在威利斯( Willis,1981)所言的“部分洞察”(partial penetration)的层
面,即虽然存在对教育不平等进行抵抗的相应行为表达,但未能洞察教
育不平等的本质,这种抵抗行为本身可被归类为“片面抵抗”,即青少年
只对抗学校场域中微观层面的日常教育实践, 而没有抵抗宏观层面的
阶级关系和文化霸权,通常仅表现为反动行为、自食其果型抵抗和顺从
型抵抗(李淼、熊易寒,2024,2017)。 在这种情况下,弱势学生的抵抗行
为也并非是顺从-抵抗这种对立二分,由于中国青少年对于通过教育实
现社会流动具有普遍期待,在感知到被学校体系边缘化时,其对于顺从
型抵抗和自食其果型抵抗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学校和教师能否为其实现
社会流动的目标提供效用, 甚至可能出现同时采取两种抵抗行动的可
能性(李淼、熊易寒,2017)。
教师 对 学 生 的态 度 和 行为直 接 影 响 学生 对 其 社 会 流 动 前 景 的 评
估,如果教师对学生学业发展展现负责态度、提出相应要求,弱势学生
更可能采取顺从型抵抗策略。 反之,如果教师对学生具有先在的隐性偏
·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