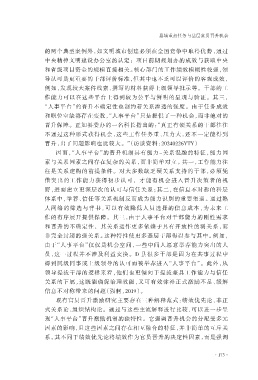Page 180 - 《社会》2025年第3期
P. 180
县域重点任务与基层官员晋升机会
的两个典型案例外,如文明城市创建必须在全国竞争中取得优势,通过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的认定; 项目前期规划办的成效与获取中央
和省级项目资金的规模直接相关。 核心部门的工作绩效模糊性较强,领
导认可是更重要的干部评价标准,但其中也不乏可以评价的客观成效,
例如,发现较大案件线索、撰写的材料获得上级领导批示等。 干部的工
作能力可以在这些平台上得到较为公平与鲜明的呈现与验证。 其三,
“人事平台”的晋升不确定性也制约着关系渗透的强度。 由于任务成效
和职位空缺都存在变数,“人事平台”只是提供了一种机会,而非绝对的
晋升保障。 正如县委办的一名科长指出的:“真正有硬关系的干部往往
不通过这种形式获得机会,这些工作任务重、压力大,还不一定能得到
晋升,出了问题影响也比较大。 ”(访谈资料:20240226YTY)
因而,“人事平台”的晋升机制具有能力-关系混融的特征,能力因
素与关系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而非简单对立。 其一,工作能力往
往是关系建构的前提条件。 对大多数缺乏硬关系支持的干部,必须凭
借突出的工作能力获得初步认可, 才能 有 机会进 入 晋升决 策 者 的视
野,进而建立更深层次的认可与信任关系;其二,在信息不对称的科层
体系中,举荐、信任等关系机制反而成为能力识别的重要渠道。 通过熟
人网络的筛选与背书,可以有效降低人员选择的信息成本,为未来工
作的有序展开提供保障。 其三,由于人事平台对干部能力的刚性需求
和晋升的不确定性, 其关系运作更多依赖于具有开放性的弱关系,而
非完全封闭的强关系。 这种特性使更多基层干部得以参与其中。 例如,
由于“人事平台”仅仅是机会空间,一些中间人愿意举荐能力突出的人
员,这一过程并不涉及利益交换。 D 县很多干部是因为在共事过程中
得到同级同事或上级领导的认可而被举荐进入“人事平台”。 此外,从
领导提拔干部的逻辑来看,他们也更倾向于提拔兼具工作能力与信任
关系的下属,这既能确保治理效能,又可有效弥补正式激励不足、缓解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强舸,2019)。
现有官员晋升激励研究主要存在三种解释范式:绩效优先论、非正
式关系论、组织结构论。 通过与这些主流解释进行比较,可以进一步呈
现“人事平台”晋升激励机制的独特性。 它强调晋升机会的分配受多元
因素的影响,且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相互融合的特征,并非简单的互斥关
系。 其不同于绩效优先论将绩效作为官员晋升的决定性因素,而是强调
· 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