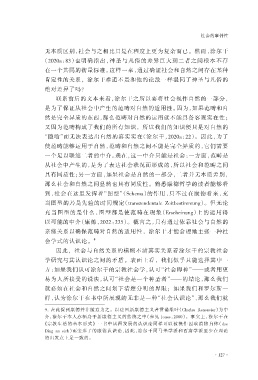Page 134 - 《社会》2025年第3期
P. 134
社会的事件性
无本质区别,社会与之相比只是在程度上更为复杂而已。 然而,涂尔干
(2020a:83)也明确指出,神圣与凡俗的差异巨大到二者之间根本不存
在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 这样一来,通过确证社会和自然之间存在某种
肯定性的关系, 涂尔干难道不是和他的论敌一样混同了神圣与凡俗的
绝对差异了吗?
联系前后的文本来看,涂尔干之所以要将社会视作自然的一部分,
是为了保证从社会中产生的范畴对自然的适用性。 因为,如果范畴和自
然是完全异质的东西,那么范畴对自然的运用就不能具备客观实在性;
又因为范畴构成了我们的所有知识, 所以我们的知识便只是对自然的
“隐喻”而无法表达出自然的真实实在(涂尔干,2020a:22)。 因此,为了
使范畴能够运用于自然,范畴和自然之间不能是完全异质的,它们需要
一个足以联结二者的中介。现在,这一中介只能是社会:一方面,范畴是
从社会中产生的,是为了表达社会状况而形成的,所以社会和范畴之间
具有同质性;另一方面,如果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二者并无本质差别,
那么社会和自然之间显然也具有同质性。 熟悉康德哲学的读者能够看
到,社会在这里发挥着“图型”(Schema)的作用,只不过在康德看来,充
当图型的乃是先验的时间规定(transzendentale Zeitbestimmung)。 但无论
充当图型的是什么,图型都是使范畴 在现 象(Erscheinung)上的运 用 得
以可能的中介(康德,2022:235)。 概言之,只有通过依靠社会与自然的
亲缘关系以确保范畴对自然的适用性, 涂尔干才能合理地主张一种社
会学式的认识论。 9
因此, 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模糊不清其实关系着涂尔干的宗教社会
学研究与其认识论之间的矛盾。 表面上看, 我们似乎只能选择其中一
方:如果我们认可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认可“社会即神”———或者用更
易为人所接受的说法,认可“社会是一个神圣者”———的结论,那么我们
就必须在社会和自然之间划下清楚分明的界限; 如果我们和罗尔斯一
样,认为涂尔干在书中所展现的无非是一种“社会认识论”,那么我们就
9. 在此提到康德并非随意为之。 以法国新康德主义者雷诺维叶(Charles Renouvier)为中
介,涂尔干本人亦栖身于新康德主义的传统之中(参见 Jones,2000)。 事实上,涂尔干在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一书中试图发展的认识论同样可以被 视作因 取消物 自体( das
Ding an sich)而变形了的康德认识论,因此,涂尔干同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至少在理论
的出发点上是一致的。
·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