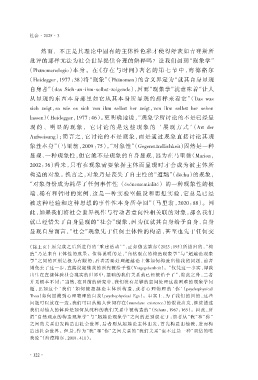Page 129 - 《社会》2025年第3期
P. 129
社会·2025·3
然而, 不正是其理论中固有的主体性色彩才使得舒茨如吉登斯所
批评的那样无法为社会世界提供合理的解释吗? 让我们回到“现象学”
(Ph覿nomenologie)本 身 。 在《存 在 与 时 间》著 名 的 第 七 节 中 , 海 德 格 尔
(Heidegger,1977:38)将“现象”(Ph覿nomen)的含义界定为“就其自身显现
自身者”(das Sich鄄an鄄ihm鄄selbst鄄zeigende),因而“现象学”就意味着“让人
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Das was
sich zeigt,so wie es sich von ihm selbst her zeigt,von ihm selbst her sehen
lassen)(Heidegger,1977:46)。 更明确地说,“现象学所讨论的不是已经呈
现 的 、 明 显 的 现 象 , 它 讨 论 的 是 这 些 现 象 的 ‘展 现 方 式 ’( Art der
Aufweisung);简言之,它讨论的不是现象,而是通过现象直接讨论其现
象性本身”(马里翁,2009:75)。“对象性”(Gegenst覿ndlichkeit)固然是一种
显现、一种现象性,但它绝不是现象的自身显现,因为在马里翁(Marion,
2002:36)看来,只有在现象需要依据主体而显现时才会成为被主体所
构造的对象。 换言之,对象乃是丧失了自主性的“遭黜”( déchu)的现象,
“对象身份成为耗尽了任何事件性 (événementialité) 的一种现象性的极
端、稀有和暂时的案例,这是一种实验室假设和思想实验,它总是已经
被这种经验和这种思想的事件性本身所夺回”(马里翁,2020:88)。 因
此,如果我们将社会世界视作与行动者意向性相关联的对象,那么我们
就已经错失了自身显现的“社会”现象,因为仅就其自身给予自身、自身
显现自身而言,“社会”现象先于任何主体性的构造,甚至也先于任何交
(接上页) 原完成之 后所进行的‘重建活动 ’”,正如伽达默尔(2023:195)所指出的,“构
造”乃是来自主体性的成果。 值得说明的是,“自然观点的构造现 象学”与“超越论现 象
学”之间的区别是极为有限的:后者需要处理超越论主体如何构 造出他我 的问题,前者
则免去了这一步,直接设定他我的预先被给予性(Vorgegebenheit)。“仅凭这一事实,即我
出生在直接体验社会现实的世界中,基础的我们关系就已经被给予了”,除此之外,二者
并无根本不同:“当然,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处理这些困难的现象学问
题 , 比 如 这 个‘我 们 ’ 如 何 被 超 越 论 主 体 所 构 造 , 或 者 心 理 物 理 的‘你 ’(psychophysical
Thou)如何回溯到心理物理的自我(psychophysical Ego)。 事实上,为 了我们 的目的,这些
问题可以放在一边。 我们可以从他人世间存在(mundane existence)的假设出发,继续描述
我们对他人的体验是如何从纯粹的我们关系中被构造的”(Schutz,1967:165)。 因此,所
谓“自然观点的构造现象学”与“超越论现象学”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前者从“我”和“你”
之间的关系出发构造出社会世界,后者 则从超越论主体出发,首先构 造出他我 ,进而构
造出社会世界。 但是,作为“我”和“ 你”之间关系的“我们关系”也不过是一种“双倍的唯
我论”(海德格尔,2018:411)。
· 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