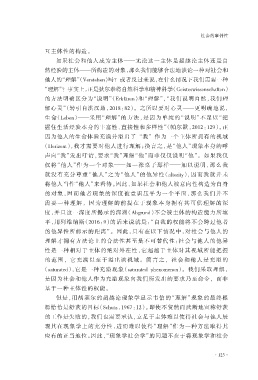Page 130 - 《社会》2025年第3期
P. 130
社会的事件性
互主体性的构造。
如果社会和他人成为主体———无论这一主体是超越论主体还是自
然经验的主体———所构造的对象,那么我们能够合法地谈论一种对社会和
他人的“理解”(Verstehen)吗? 或者反过来说,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一种
“理解”? 事实上,正是狄尔泰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
的方法明确区分为“说明”(Erkl覿ren)和“理解”,“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
解心灵”(转引自洪汉鼎,2018:82)。 之所以要对心灵———更明确地说,
生命( Leben)———采用“理解”的方法,是因为单纯的“说明”不足以“把
握住生活经验本身的丰富性、直接性和多样性”(帕尔默,2012:129)。正
因为他人的生命体验充满并溢出了“我” 作为一个主体所拥有的视域
( Horizont),我才需要对他人进行理解;换言之,是“他人”现象本身的呼
声向“我”发出吁请,要求“我”理解“他”而非仅仅说明“他”。 如果我仅
—
仅将“他人”作为一个对象——如一张桌子那样———加以说明,那么我
就没有充分尊重“他人”之为“他人”的他异性( alterity),因而我就并未
将他人当作“他人”来看待。因此,如果社会和他人被意向性构造为自身
的对象,因而他者现象的深度被意识压平为一个平面,那么我们并不
需要一种理解, 因为理解的前提在于现 象本身 拥 有 其 可 供 理 解 的 深
度,并且这一深度所揭示的深渊(Abgrund)不会被主体的构造能力所填
平,用列维纳斯( 2016:9)的话来说就是:“自我的权能将不会跨过他者
的他异性所标示的距离”。 因此,只有在以下情况中,对社会与他人的
理解才拥有方法论上的合法性甚至是不可替代性:社会与他人的他异
性是一种相对于主体的绝对外在性,它超越于主体对其视域所能把握
的 范 围 , 它 充满以至于溢出该视域。 简言之 , 社会和 他人 是充 溢 的
( saturated),它是一种充溢现象(saturated phenomenon)。 我们采取理解,
是因为社会和他人作为充溢现象向我们所发出的要求乃至命令, 而非
基于一种主体性的权能。
但是,用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显示韦伯的“理解”现象的最终根
源恰恰是舒茨的目标(Schutz,1967:12)。 即使不贸然而武断地宣称舒茨
的工作是失败的,我们也需要承认,立足于主体难以使得社会与他人展
现其在现象学上的充分性,进而难以使得“理解”作为一种方法取得其
应有的正当地位。因此,“现象学社会学”的问题不在于将现象学和社会
·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