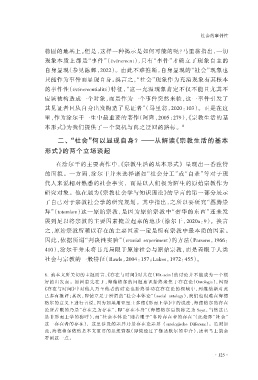Page 132 - 《社会》2025年第3期
P. 132
社会的事件性
稳固的地基上。但是,这样一种揭示是如何可能的呢?马里翁指出,一切
现象本质上都是“事件”(événement),只有“事件”才确立了现象自主的
自身显现(参见陈辉,2022)。 由此不难推断,自身显现的“社会”现象也
只能作为事件而显现自身。换言之,“社会”现象作为充溢现象有其根本
的事件性(événementialité)特征,“这一充溢现象肯定不仅不能且尤其不
应该被构造成一个对象,而是作为一个事件突然来临,这一事件引发了
其见证者且从自身出发构造了见证者”(马里翁,2020:103)。 正是在这
里,作为涂尔干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阿隆,2005:279),《宗教生活的基
本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与向之迂回的路标。 8
二、“社会”何以显现自身? ———从解读《宗教生活的基本
形式》的两个立场谈起
在涂尔干的主要著作中,《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呈现出一番独特
的面貌。 一方面,涂尔干并未选择诸如“社会分工”或“自杀”等对于现
代人来说相对熟悉的社会事实, 而是以人们极为陌生的原始宗教作为
研究对象。 他在题为《宗教社会学与知识理论》的导言的第一部分展示
了自己对于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规划。 其中指出,之所以要研究“图腾崇
拜”(totemism)这一原始宗教,是因为原始宗教中“奢华的东西”还未发
展到足以将宗教的主要因素掩盖起来的地步(涂尔干,2020a:9)。 换言
之,原始宗教所赖以存在的主要因素一定是所有宗教中最本质的因素。
因此,依据所谓“判决性实验”(crucial experiment)的方法(Parsons,1966:
410),涂尔干并未将目光局限于原始社会与原始宗教,而是着眼于人类
社会与宗教的一般特征(Rawls,2004:157;Lukes,1972:455)。
8. 就本文所关切的主题而言,《存在与时间》对共在(Mit鄄sein)的讨论并不能成为一个很
好的出发点。 原因首先在于,海德格尔的问题意识始终聚焦于存在论(Ontologie),因而
《存在与时间》中对他人乃至他者的讨论也始终活动在存在论的视域中,列维纳斯对此
已多有批评;其次,即使立足于所谓的“社会本体论”( social ontology),我们也很难在海德
格尔的意义上进行言说,因为如果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说法,海德格尔的存在
论所着眼的乃是“存在之为存在”,即“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后期称之为 Seyn,当然这已
是非形而上学的称呼),而“社会本体论”则着眼于“各种存在者的存在”(此处即“社会”
这一存在者的存在), 这里涉及的差异乃是存在论差异 ( ontologische Differenz)。 虽则如
此,海德格尔依然是本文重要的思想资源(即使经过了伽达默尔的中介),读者马上就会
看到这一点。
· 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