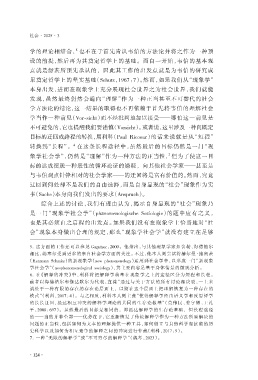Page 131 - 《社会》2025年第3期
P. 131
社会·2025·3
5
学的理论相结合, 也不在于首先肯认韦伯的方法论并将之作为一种预
设的前提,然后再为其奠定哲学上的基础。 而自一开始,韦伯的基本观
点就是舒茨所预先承认的, 因此其工作的出发点就是为韦伯的研究成
果奠定哲学上的坚实基础( Schutz,1967:7)。然而,如果我们从“现象学”
本身出发,进而在现象学上充分展现社会世界之为社会世界,我们就能
发现,虽然最终仍然会通向“理解”作为一种正当甚至不可替代的社会
学方法论的结论,这一结果的取得也不再依赖于首先将韦伯的理解社会
学当作一种前见( Vor鄄sicht)而不经批判地加以接受———哪怕这一前见是
不可避免的,它也提醒我们要谨慎( Vorsicht)。 或者说,这里涉及一种向既定
目标的迂回或路程的转换,用利科( Paul Ricoeur)的话来说就是从“短程”
转换到“长程”。 6 在这条长程途径中,虽然最后的目标仍然是一门“现
7
象学社会学”,仍然是“理解”作为一种方法的正当性, 但为了使这一目
—
标的达成摆脱一种恶性的循环论证的嫌疑, 向其他社会学家——甚至是
—
与韦伯观点针锋相对的社会学家——的迂回将是富有价值的。然而,究竟
迂回到何处却不是我们的自由选择,而是自身显现的“社会”现象作为实
事( Sache)本身向我们发出的要求(Anspruch)。
综合上述的讨论,我们有理由认为,揭示自身显现的“社会”现象乃
是一门“现象学社会学”(ph覿nomenologische Soziologie)的题中应有之义,
也是其必须由之启程的出发点。 如果我们没有在现象学上恰当地对“社
会”现象本身做出合理的规定,那么“现象学社会学”就没有建立在足够
5. 这方面的工作还可以参见 Gugutzer,2000。 他指出,与其他现象学家如舍勒、海德格尔
相比,胡塞尔受到更多的来自社会学方面的关注。 不过,他本人则尝试将赫尔曼·施密茨
( Hermann Schmitz)的新现象学(new phenomenology)运用到社会学中,以形成一门“新现象
学社会学”(neo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其主要内容是基于身体情景的微观分析。
6. 在《解释的冲突》中,利科将把解释学奠基 在现象 学之上 的途径区分 为 短 程 和长 程 。
前者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 表,直接“通过与 关于方法的所 有讨论相决裂,一上来
就处于一种有限的存在的存在论层面上, 以期在这个层面上把理解恢复为一种存在的
模式”(利科,2017:4)。 与之相反,利科本人则主张“使得解释学经由语义学和反思哲学
的长长迂回,抵达相互冲突的解释学理论的共同的生存论根基”(莫伟民、姜宇辉、王礼
平,2008:697)。 虽然最后的目标是相同的, 即抵达解释学的生存论基础, 但长程途径
—
的——当然并非全部———优势在于,它重新恢复了传统解释学作为一种方法所要解决的
问题的正当性,包括如何为文本的理解提供一种工具,如何创立与自然科学相抗衡的历
史科学以及如何为相互竞争的解释之间的冲突进行仲裁(利科,2017:9)。
7. 一种“无限的解释学”或“不可穷尽的解释学”(魏琴,2023)。
· 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