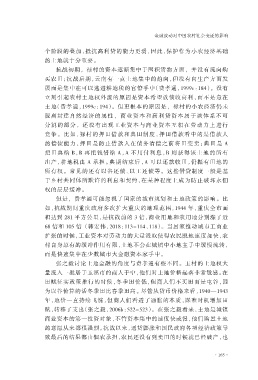Page 172 - 《社会》2025年第2期
P. 172
金融波动对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个阶段的叠加,抵抗高利贷的能力更弱,因此,保护作为小农经济基础
的土地就十分重要。
抗战初期, 禄村的资本逐渐集中于囤积货物方面, 并没有流向购
买农田;抗战后期,云南有一点土地集中的趋向,但没有向生产方面发
展而是集中在可以逃避耕地税的官僚手中(费孝通,1999c:184)。 没有
立刻引起农村土地权外流的原因是资本希望放债收高利,而不是意在
土地(费孝通,1999c:194)。 但更根本的原因是, 禄村的小农经济仍未
脱离封建自然经济的属性 , 商 业 资 本 和 高利贷资 本 属 于 该 体系 不 可
分割的部分, 还没有出现工业资本与商 业 资 本 互 相 在 劳 动 力上 进行
竞争。 比如,禄村的押田借款和典田制度,押田借款看中的是借款人
的偿债能力,押田是防止借款人在债务清偿之前 将 田 变卖 ;典 田 是 A
把田典给 B,B 再把钱借给 A,A 不用付利息,B 则 获 得 该 土 地的 所 有
出产,耕地税由 A 承担。 典期结束后,A 可以还款收田,仍据有田地的
所有权。 常见的还有以谷还债、以工还债等。 这些借贷制度一般是基
于乡村共同体所默许的利息和契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防止破坏永佃
权的层层缓冲。
但是, 费孝通可能忽视了国家的城市规划和土地政策的影响。 比
如,抗战期间重庆政府多次扩大重庆的地理范围,1944 年,重庆全市面
积达到 281 平方公里,是抗战前的 3 倍,商业用地和农用地分别涨了近
68 倍和 105 倍 (韩宏伟,2018:113-114、118)。 当国家推动城市工商业
扩张的时候,工业资本对劳动力的大量汲取使得农民脱地速度加快,农
村自身原有的缓冲作用有限,土地不会在城镇中小地主手中缓慢流转,
而是快速集中在少数城市大金融资本家手中。
张之毅讨论土地金融的角度与费孝通有些不同。 玉村的土地权大
量流入一批居于玉溪市的商人手中,他们对土地价格起落非常敏感。 在
田赋征实政策推行的时候,冬季田价低,但商人们不买田而是屯谷,因
为以谷价算的话冬季田比春季田高。 尽管从货币价格来看,1940—1943
年,地价一直持续飞涨,但商人们看透了通胀的本质,踩准时机增加田
赋,转移了支出(张之毅,2006b:522-523)。 在张之毅看来,土地是城镇
商业资本的第一投资对象,不管资本集中的速度快或慢,他们购置土地
的意愿从来都很强烈。 抗战以来,通货膨胀和国民政府各项经济政策导
致最后的结果都由佃农承担,农民还没有到卖田的时候就已经破产,也
·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