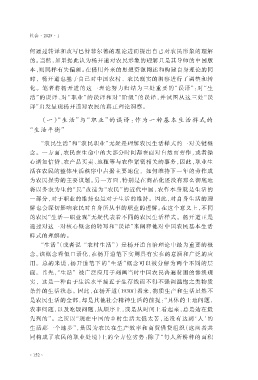Page 159 - 《社会》2025年第1期
P. 159
社会·2025·1
何通过转译和改写巴特菲尔德的理论进而提出自己对农民形象的理解
的。 当然,如果据此认为杨开道对农民形象的理解只是其导师的中国版
本,则同样有失偏颇。 在借用外来的思想资源阐述和构建自身理论的同
时, 杨开道也基于自己对中国农村、 农民现实的洞察进行了调整和转
化。 笔者将杨开道的这一理论努力归结为三处重要的“误译”:对“生
活”的误译、对“职业”的误译和对“阶级”的误译,并试图从这三处“误
译”出发呈现杨开道对农民的真正理论洞察。
(一)“生活”与“职业”的误译:作为一种基本生活样式的
“生活平衡”
“农民生活”和“农民职业”无疑是理解农民生活样式的一对关键概
念。 一方面,农民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面对自然而劳作,或者操
心诸如信贷、农产品买卖、地租等与农作紧密相关的事务,因此,职业生
活在农民的整体生活秩序中占据主要地位, 如何维持下一年的劳作成
为农民操劳的主要议题。 另一方面,特别是在商品化还没有那么彻底地
将以务农为生的“民”改造为“农民”的近代中国,农作本身就是生活的
一部分,对于职业的维持也是对于生活的维持。 因此,对自身生活的理
解也会深切影响农民对自身所从事的职业的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不同
的农民“生活—职业观”无疑代表着不同的农民生活样式。 杨开道正是
通过对这一对核心概念的转写和“误译”来阐释他对中国农民基本生活
样式的理解的。
“生活”(或者说“农村生活”) 是杨开道自治理论中最为重要的概
念。 该概念看似口语化,在杨开道笔下实则具有实在的意涵和广泛的应
用。 总的来说,杨开道笔下的“生活”概念可以被分解为两个不同的层
面。 首先,“生活” 被广泛应用于刻画当时中国农民普遍贫困的惨淡现
实, 这是一种由于生活水平接近于生存线而不得不强调温饱之类物质
条件的生活状态。 因此,在杨开道(1930f)看来,物质生产和生活虽然不
是农民生活的全部,却是其他社会精神生活的前提:“具体的土地问题,
农事问题,以及吃饭问题,从顺序上,或是从时间上看起来,总是站在最
先列的”。 之所以“现在中国的乡村生活太低太苦,还没有达到‘人’的
生活那一个地步”,是因为农民在生产效率和商贸借贷组织(这两者共
同构成了农民的职业处境)上的全方位劣势:除了“每人所耕种的面积
· 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