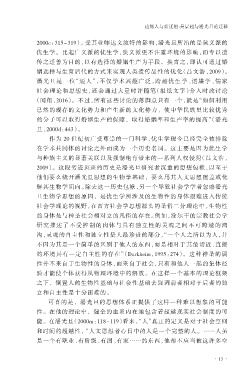Page 20 - 《社会》2024年第4期
P. 20
边缘人与始迁祖:吴景超与潘光旦论迁移
2000e:315-319)。 受其业师达文波特的影响,潘光旦所治的是狭义派的
优生学。 比起广义派的优生学,狭义派更不注重环境的影响,而专以遗
传之迁善为目的,以有选择的婚姻生产为手段。 换言之,即认可通过婚
姻选择与生育后代的方式来实现人类遗传品性的优化(吕文浩,2009)。
潘光旦是一位“通人”,不仅学术兴趣广泛,跨越优生学、谱牒学、儒家
社会理论和思想史,还会通过大量时评随笔(报纸文字)介入时政讨论
(闻翔,2016)。 不过,所有这些讨论的落脚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利用
已然的现存的文化势力和产生新的文化势力, 使中华民族里比较优秀
的分子可以取得婚姻生产的保障, 取得婚姻率和生产率的提高”(潘光
旦,2000d:443)。
作为 20 世纪初广受尊崇的一门科学,优生学现今已经完全被排除
在学术共同体的讨论之外而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这主要是因为优生学
与种族主义的显著关联以及强制绝育带来的一系列人权侵犯(吕文浩,
2009)。 这段劣迹斑斑的历史是潘光旦研究者沉重的思想包袱,以至于
他们要么绕开潘光旦思想的生物学基础, 要么用其人文思想覆盖或化
解其生物学面向。 除去这一历史包袱,另一个导致社会学学者忽略潘光
旦生物学思想的原因, 是优生学所涉及的生物性的身体很难进入传统
社会学理论的视野,在西方社会学思想源头的圣俗二分理论中,生物性
的身体是与神圣社会相对立的凡俗的存在。 例如,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
研究描述了不受控制的肉体与具有独立性的灵 魂 之 间 不 可 跨 越 的鸿
沟,灵魂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人最珍贵的部分,“一个人之所以为人,并
不因为其是一个简单的区别于他人的东西,而是相对于其最切近、直接
的环境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存在”(Durkheim,1995:274)。 这种神圣的属
性并不来自于生物性的身体,而来自于社会,只有和他人一起的集体经
验才能使个体获得从物理环境中的解放。 在这样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之下, 倒置人的生物性基础与社会性基础去强调前者相对于后者的独
立和自主性是十分困难的。
可喜的是, 潘光旦的思想体系正提供了这样一种难以想象的可能
性。 在他的理论中, 健全的血系内在地包含着超越现实社会制度的可
能。 在潘光旦(2000m:118-119)看来,“人”真正的定义是对于社会空间
和时间的超越性,“人文思想者心目中的人是一个完整的人。 ……人虽
是一个有职业、有阶级、有国、有家……的东西,他却不应当被这许多空
·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