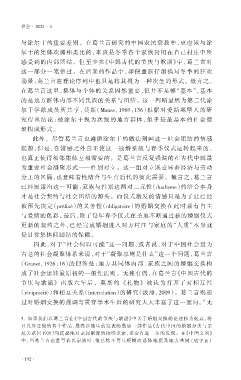Page 199 - 《社会》2024年第4期
P. 199
社会·2024·4
与涂尔干的重要差别。 在葛兰言研究的中国农民宗教中,更应该与涂
尔干的集体欢腾相类比的,本该是冬季各个家族封闭在自己村庄中所
感受到的内部团结。 但至少在《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葛兰言对
这一部分一笔带过。 在后来的作品中,即便重新仔细描写冬季的狂欢
场景,葛兰言在理论序列中也只是将其视为一种次生的形式。 概言之,
在葛兰言这里,集体与个体的关系固然重要,但并不足够“基本”,基本
的是地方群体内部不同氏族的关系与团结。 这一判断显然为第二代涂
尔干学派成员所共享,莫斯( Mauss,1969:136)根据对爱斯基摩人的研
究得出结论:被涂尔干视为次级的地方群体,似乎是最基 本 的社会凝
聚构成形式。
此外, 尽管葛兰言也遵循涂尔干的做法刻画这一社会团结的情感
起源,但是,在情感之外真正使这一通婚系统与春季仪式运转起来的,
也真正使得相邻集体互相需要的, 是葛兰言反复强调的在古代中国最
为重要社会凝聚形式——性别对立。 这一组对立既意味着经济与劳动
—
分工的区隔,也意味着性结合与生育后代的彼此需要。 概言之,葛兰言
已经展露出这一可能:家族与性别这两对二元性( dualisme)的结合本身
才是社会契约与社会团结的源头。 而仪式激发的情感只是为了让已经
被预先决定(préfixé)的义务性(obligatoire)的婚姻交换在此时兼有自主
与爱情的色彩。 最后,除了每年春季仪式在圣地不断通过新的婚姻仪式
更新的契约之外,已经完成婚姻进入对方村庄与家庭的“人质”本身就
是日常集体间团结的保障。
因此,对于“社会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或者说,对于中国社会最为
古老的社会凝聚体系来说,对于“凝聚原则是什么”这一个问题,葛兰言
( Granet,1926:16)的回答是:地方共同体内部、家族之间的婚姻交换构
成了社会运转最原初的一般性法则。 无独有偶,在葛兰言《中国古代的
节庆与歌谣》 出 版 六 年 后 , 莫 斯 的 《礼 物》 被 认 为 打开 了 对 相 互 性
( réciprocité)和相互关系(interrelation)的研究(汲喆,2009)。 葛兰言则通
5
过对婚姻交换的强调与贯穿学术生涯的研究大大丰富了这一面向。 无
5. 如果我们以葛兰言在《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中关于婚姻交换的论述作为起点,将
目光穿过他的各个作品,最终以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古代中国的婚姻分类与亲
属关系》(1939)勾连起他对亲属制度的持续求索,还会有进一步的发现。 在《中国文明》
中,当葛兰言在重写农民宗教时 ,他已然 不再只 模糊而 总体 地 提及地 方 共 同(转下页)
· 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