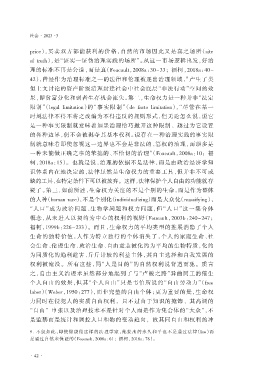Page 49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49
社会·2023·3
price),买卖双方都能获利的价格,自然的市场因此又是真之场所(site
of truth),是“证实—证伪治理实践的场所”。 从这一市场逻辑出发,好治
理的标准不再是公道,而是真(Foucault,2008a:30-33; 福柯,2018a:40-
9
42),曾经作为治理标准之一的法律和伦理被逐出治理领域, 产生了类
似上文讨论的资产阶级清理封建社会中社会底层“非法行动”空间的效
果,即贫富分化和弱者生存机会流失。第二,生命权力是一种并非“法定
限制”( legal limitation)的“事实限制”(de facto limitation),“尽管在某一
时刻法律不得不将之改编为不得违反的规则形式,但无论怎么说,说它
是一种事实限制就意味着如果治理恰巧撇开这种限制、 越过为它设置
的各种边界,仍不会被剥夺其基本权利。 说存在一种治理实践的事实限
制就意味着即使忽视这一边界也不会是非法的、篡权的治理,而顶多是
一种未能做正确之事的笨拙的、不恰切的治理”( Foucault,2008a:10; 福
柯,2018a:15)。 也就是说,治理的依据不是法律,而是由政治经济学知
识体系内在地决定的,法律虽然是生命权力的重要工具,但并非不可或
缺的工具,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被放弃。 这样,法律保护个人自由的功能就存
疑了。 第三,如前所述,生命权力关注的不是个别的生命,而是作为整体
的人种(human race),不是个别化(individualizing)而是大众化(massifying),
“ 人口”成为政治问题、生物学问题和权力问题,但“人口”这一集合体
概念,从未进入以契约为中心的权利的视野(Foucault,2003b:240-247;
福柯,1999b:226-233)。 而且,生命权力的平均类型的推展消隐了个人
生命的独特价值,人作为特立独行的个体消失了,个人的家庭生命、社
会生命、伦理生命、政治生命、自由意志被化约为平均的生物特质,化约
为同质化的趋利避害、斤斤计较的利益主体,其自主选择和自我发展的
权利被淹没。 所有这些,同“人是目的”的自然权利说背道而驰。 质言
之,自由主义治理术虽然部分地起到了与“卢梭之路”异曲同工的催生
个人自由的效果,但其“个人自由”只是韦伯所说的“自由劳动力”(free
labor)(Weber,1950:277),而非完整的自由个体;更为重要的是,生命权
力同时在侵犯人的实质自由权利, 只不过由于知识的掩饰、 其高调的
“自由” 申张以及治理技术不是针对个人而是作为集合体的“大众”,不
是监禁而是统计和调控人口和物的变动趋向, 故其同自由和权利的冲
9. 不仅如此,即使像康德这样的法理学家,他提出的永久和平也不是通过法律(law)而
是通过自然来保证的( Foucault,2008a:61; 福柯,2018a:78)。
·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