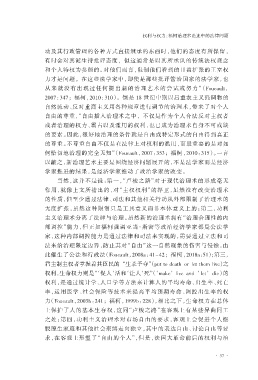Page 44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44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动及其行政管理的各种方式直接继承的东西时,他们的态度有所保留,
有时会对其诞生持批评态度, 但这通常是以其所承认的传统法权观念
和个人特权为参照的。 对他们而言,限制他们看到的日益扩张的王室权
力才是问题。 在这些法学家中,即使是那些批评管治国家的法学家,也
从 来 就没 有出 现 过 任 何 提 出 新 的治理 艺 术的 尝 试 或 努 力 ”( Foucault,
2007:347; 福柯,2010:310)。 倒是 18 世纪中期以后重农主义强调物的
自然流动、反对重商主义用各种规章进行调节的治理术,带来了对个人
自由的尊重,“自由插入治理术之中, 不仅是作为个人合法反对主权者
或者治理的权力、霸占以及滥用的权利,也已成为治理术自身不可或缺
的要素。 因此,很好地治理的条件就是自由或特定形式的自由得到真正
的尊重。 不尊重自由不仅是在法律上对权利的滥用,而最重要的是对如
何恰切地治理的完全无知”( Foucault,2007:353; 福柯,2010:315)。一言
以蔽之,新治理艺术主要是围绕经济问题展开的,不是法学家而是经济
学家推进的结果,是经济学家推动了政治学家的改变。
当然,这并不是说:第一,“卢梭之路”对于现代治理术的形成毫无
作用,就像上文所指出的,对“主权权利”的捍卫,虽然没有改变治理术
的性质,但至少通过法律、司法和其他相关行动从外部限制了治理术的
无度扩张,虽然这种限制只是工具意义而非本体意义上的;第二,功利
主义治理术分离了法律与治理。 虽然新的治理术拥有“治理合理性的内
部调控”能力,但正如福柯强调亚当·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都是公法学
家,这种内部调控能力是通过法律和司法来实现的,需要通过立法和司
法来给治理限定边界,防止其对“自由”这一自然现象的伤害与侵蚀,由
此催生了公法和行政法(Foucault,2008a:41-42; 福柯,2018a:51);第三,
君主制主权者掌握着其臣民的“生杀予夺”(put to death or let them live)之
权利,生命权力则是“‘促人’活和‘让人’死”(‘make’ live and‘let’ die)的
权利,是通过统计学、人口学等方法来计算人的平均寿命、出生率、死亡
率,运用医学、社会保险等技术来提高平均预期寿命、调控出生率的权
力(Foucault,2003b:241; 福柯,1999b:228),相比之下,生命权力在总体
上保护了人的基本生存权,这同“卢梭之路”在客观上有某些异曲同工
之处;第四,功利主义治理术对市场自由的要求,客观上会促进个人摆
脱原生家庭和其他社会束缚走向独立,其中的表达自由、讨论自由等要
求,在客观上形塑了“自由的个人”,但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权利与治
·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