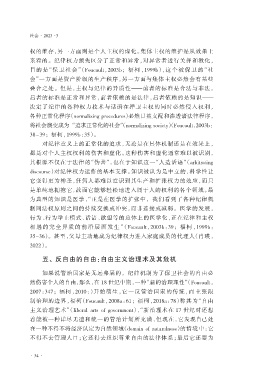Page 41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41
社会·2023·3
权的维存,另一方面则是个人主权的虚化。 集体主权的维护是从效果上
来看的。 纪律权力预先区分了正常和异常,对异常者进行关押和教化,
目 的是“保 卫 社会”(Foucault,2003b; 福 柯 ,1999b),这 个 被 保 卫 的“社
会”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生产秩序,另一方面与集体主权必然会有某些
叠合之处。 但是,主权与纪律的异质性——
—前者的标准是合法与非法,
后者的标准是正常和异常,前者依赖的是法律,后者依赖的是知识———
决定了纪律的各种权力技术与话语在捍卫主权的同时必然侵入权利,
各种正常化程序(normalizing procedures)必然日益支配和渗透诸法律程序,
将社会演变成为“追求正常化的社会”( normalizing society)(Foucault,2003b:
38-39; 福柯,1999b:35)。
对纪律意义上的正常化的追求,无论是在具体机制还是在效果上,
都是对个人主权权利的伤害和虚化。 这种伤害和虚化通常难以被识别,
其根源不仅在于法律的“伪善”,也在于知识这一“人造话语”( arbitrating
discourse)对纪律权力运作的基本支撑。 知识被认为是中立的,科学性让
它变得更为神圣,任何人都难以意识到其生产和扩张权力的效应,而只
是单纯地拥抱它,故而它能够轻松地进入属于人的权利的各个领域。 最
为典型的知识是医学,“正是在医学的扩张中, 我们看到了各种纪律机
制同法权原则之间的持续交换或冲突,而非连接或减弱。 医学的发展,
行为、行为举止模式、话语、欲望等的总体上的医学化,正在纪律和主权
相 遇 的 完 全 异 质 的 前 沿 层 面 发 生 ”(Foucault,2003b:39; 福 柯 ,1999b:
35-36)。 甚至,父母主动地成为纪律权力进入家庭成员的代理人(肖瑛,
2022)。
五、 反自由的自由:自由主义治理术及其危机
如果说管治国家是无远弗届的, 纪律机制为了保卫社会的自由必
然伤害个人的自由,那么,在 18 世纪中期,一种“新的治理理性”(Foucault,
2007:347; 福柯,2010:)开始萌生,它一反管治国家的传统,而主张限
制治理的边界,福柯(Foucault,2008a:61; 福柯,2018a:78)称其为“自由
主义治理艺术”(liberal arts of government),“新治理术在 17 世纪时还想
着能被一种详尽无遗和统一的管治计划所充满,但现在,它发现自己处
在一种不得不将经济认定为自然领域(domain of naturalness)的情境中:它
不得不去管理人口;它还得去组织尊重自由的法律体系;最后它还要为
· 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