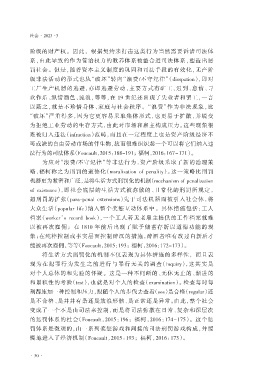Page 37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37
社会·2023·3
阶级的财产权。 因此, 根据契约来打击这类行为当然需要诉诸司法体
系,由此导致的作为管治权力的教养体系被整合进司法体系,塑造出惩
罚社会。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司法手段的有效化,无产阶
级非法活动的形式也从“破坏”转向“浪费/不守纪律”(disspation),即对
工厂生产机器的逃避,亦即逃避劳动,主要方式有旷工、迟到、怠惰、寻
欢作乐、纵情酒色、流浪,等等,在 19 世纪还出现了失业者和罢工,一言
以蔽之,就是不珍惜身体、家庭与社会秩序。“浪费”作为非法现象,比
“破坏”严重得多,因为它更容易采取集体形式,也更易于扩散,并蜕变
为拒绝工业劳动的生存方式,由此对市场和雇主构成压力。 这些现象很
难被归入违法( infraction)范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资产阶级经济不
可或缺的自由劳动市场的伴生物,故而很难组织起一个可以将它们纳入违
法行为的司法体系( Foucault,2015:188-191; 福柯,2016:167-171)。
为应对“浪费/不守纪律”等非法行为,资产阶级采取了新的治理策
略,福柯称之为刑罚的道德化(moralization of penality)。 这一策略比刑罚
机器更为紧密和广泛,是将生活方式刑罚化的机制(mechanism of penalization
of existence),即社会底层的生活方式被弥散的、日常化的刑罚所规定,
超刑罚的扩张(para鄄penal extensions)先于司法机器而被引入社会体,将
大众生活(popular life)纳入整个奖惩互动体系中。 具体措施包括:工人
档案 (worker’s record book),一个工人若无老雇主提供的工作档案就难
以被再次雇佣; 在 1810 年前后出现了赋予储蓄存折以道德功能的现
象;在纯粹控制或事实层面控制醉汉的措施,醉酒者唯有改过自新后才
能被再次雇佣,等等(Foucault,2015:193; 福柯,2016:172-173)。
将生活方式刑罚化的机制不仅表现为具体措施的多样性, 而且表
现为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进行与罪行无关的调查(inquiry),这其实是
对个人总体的和先验的怀疑。 这是一种不间断的、无休无止的、渐进的
和累积性的考验(test),也就是对个人的检查(examination)。 检查每时每
刻都施加一种控制和压力,跟随个人的步伐去查看(see)是合格(regular)还
是不合格、是井井有条还是放浪形骸、是正常还是异常。由此,整个社会
变成了一个不是由司法来控制,而是将司法弥散在日常、复杂和深层次
的惩罚体系的社会(Foucault,2015:196; 福柯,2016:174-175)。 这个惩
罚体系是微观的,由一系列奖惩游戏和间接的司法刑罚游戏构成,并缓
慢地进入了经济机制(Foucault,2015:193; 福柯,2016:173)。
·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