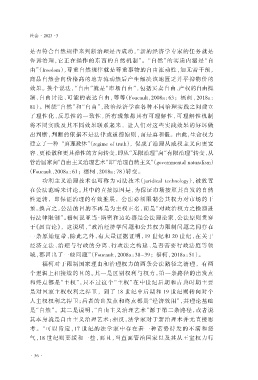Page 43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43
社会·2023·3
是否符合自然规律来判断治理是否成功,“新的经济学专家的任务就是
告诉治理,它正在操作的东西的自然机制”。“自然”的实质内涵是“自
由”(freedom),尊重自然规律就是尊重事物的自由流动性,如无需干预,
商品自然会向价格高的地方流动然后产生解决该地匮乏并平抑物价的
效果。 换个说法,“自由”就是“市场自由”,包括买卖自由、产权的自由操
演、自由讨论、可能的表达自由,等等( Foucault,2008a:63; 福 柯 ,2018a:
81)。 围绕“自然”和“自由”,政治经济学在各种不同治理实践之间建立
了理性化、反思性的一致性,所有现象都具有可理解性,可理解性机制
将不同实践及其不同效果联系起来, 让人们对这些实践效果的好坏做
出判断,判断的依据不是法律或道德原则,而是真和假。 由此,生命权力
建立了一种“真理政体”( regime of truth), 促成了治理从威权主义向更宽
容、更松散和更具弹性的方向转变,即从“无限治理”向“有限治理”转变,从
管治国家向“自由主义治理艺术”即“治理自然主义”(governmental naturalism)
(Foucault,2008a:61; 福柯,2018a:78)转变。
功利主义治理技术也可称为司法技术(juridical technology),被放置
在公法范畴来讨论。 其中的直接原因是,为保证市场按照其自发的自然
性运转, 即保证治理的有效推展, 公法必须限制公共权力对市场的干
预。换言之,公法的目的不再是为主权正名,而是“对政治权力之操演进
行法律限制”。福柯说亚当·斯密和边沁都是公法理论家,公法原则贯穿
于《国富论》, 这说明,“政治经济学问题和公共权力限制问题之间存在
一条原始纽带,除此之外,有大量证据证明,19 世纪和 20 世纪,在关于
经济立法、治理与行政的分离、行政法之构建、是否需要行政法庭等领
域,都冒出了一些问题”(Foucault,2008a:38-39; 福柯,2018a:51)。
福柯对于限制国家理由和治理权力的两条公法路径之清理, 有两
个逻辑上相接续的目的。其一是区别权利与权力。第一条路径的出发点
和终点都是“主权”,只不过这个“主权”在中世纪后期和古典时期主要
是对国家主权权利之捍卫, 到了 18 世纪中后期和 19 世纪则转向对个
人主权权利之捍卫;后者的出发点和终点都是“经济效用”,其理论基础
是“自然”。 其二是说明,“自由主义治理艺术”源于第二条路径,或者说
其本身就是自由主义治理艺术;相反,法学家对于新治理术并无直接思
考。“可以肯定,17 世纪的法学家中存在着一种蓄势待发的不满和怒
气,18 世纪则要缓和一些,而且,当直面管治国家以及其从王室权力行
·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