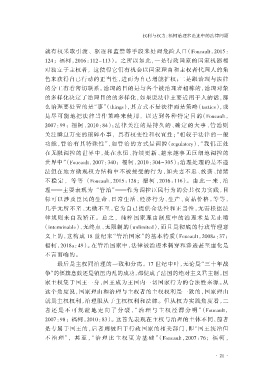Page 28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28
权利与权力:福柯治理术论述中的法律问题
就有权采取引渡、 驱逐和监禁等手段来处理危险人口(Foucault,2015:
124; 福柯,2016:112-113)。 之所以如此,一是行政国家的国家机器相
对独立于主权者, 这使得它们有机会以国家理由和主权者代理人的角
色来获得自己行动的正当性,进而为自己增能扩权;二是跟治理与法律
的分工有着密切联系。 治理的目的是与各个被治理者相称的,治理对象
的多样化决定了治理目的的多样化,如果说法律主要适用于人的话,那
么治理要处置的是“事”( things),其方式不是法律而是策略(tactics),或
是尽可能地把法律当作策略来使用, 以达到各种特定目的(Foucault,
2007:99; 福柯,2010:84);法律关注的是持久的、确定的大事,管治则
关注瞬息万变的琐碎小事, 具有权变性和权宜性;“相较于法律的一般
功能,管治有其特殊性”,如管治的方式是调控( regulatory),“我们正处
在无限调控的世界中,处在永恒、持续更新、越来越事无巨细地调控的
世界中”(Foucault,2007:340; 福柯,2010:304-305);治理处理的是不违
法但在地方微观权力结构中不被接受的行为,如夫妻不忠、放荡、情绪
不 稳 定 , 等 等 (Foucault,2015:128; 福 柯 ,2016:116)。 由 此 一 来 , 治
—
理——主要表现为“管治”———作为调控臣民行为的公共权力实践,目
标可以涉及臣民的生命、日常生活、经济行为、生产、商品价格,等等,
几乎无所不至、无微不至,它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无需根据法
律规则来自我矫正。 总之, 纯粹国家理由 制 度 中的治理术是 无 止 境
(interminable)、无终点、无限制的(unlimited),而且是彻底的行政管理意
义上的,这构成 18 世纪末“管治国家”的基本特质(Foucault,2008a:37;
福柯,2018a:49)。 在管治国家中,法律被治理术刺穿和渗透甚至虚化是
不言而喻的。
最后是主权同治理的一致和分离。 17 世纪中叶,无论是“三十年战
争”的偃旗息鼓还是镇压内乱的成功,都促成了法国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国
家主权集于国王一身,国王成为王国内一切国家行为的合法性来源。 从
这个角度说,国家理由和治理与主权者的主权权利是一致的,国家理由
就是主权权利,治理服从于主权权利和法律。 但从权力实践角度看,二
者 还 是 不 可 规 避 地 走 向 了 分 裂 ,“治 理 与 主 权 泾 渭 分 明 ”(Foucault,
2007:98; 福柯,2010:83)。 这首先表现在主权与治理的主体不同,前者
是专属于国王的,后者则被归于行政国家的相关部门,即“国王统治但
不 治 理 ”, 甚 至 ,“治 理 比 主 权 更 为 基 础 ”(Foucault,2007:76; 福 柯 ,
·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