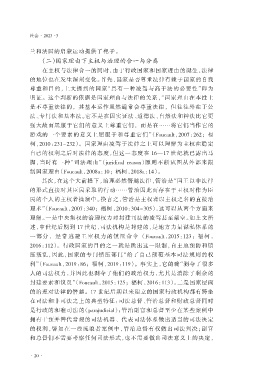Page 27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27
社会·2023·3
兰和法国的启蒙运动提供了靶子。
(二)国家理由下主权与治理的合一与分离
在主权与法律合一的同时,由于行政国家和国家理由的诞生,法律
的地位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首先,国家是否尊重法律有赖于国家的自我
尊重和目的,上文提到的国家“具有一种凌驾与高于法的必要性”即为
明证。 这个判断的依据是国家理由与法律的关系,“国家理由在本性上
是不尊重法律的, 其基本运作虽然通常会尊重法律, 但往往外在于公
法、专门法和基本法。它不是在因实证法、道德法、自然法和神法比它更
强大故而屈服于它们的意义上尊重它们, 而是在……将它们当作它的
游戏的一个要素的意义上屈服于和尊重它们”( Foucault,2007:262; 福
柯,2010:231-232)。 国家理由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理解为主权在稳定
自己的权利之后对法律的态度,但这一态度在 16—17 世纪就已露出马
脚,当时有一种“司法理由”( juridical reason)原则不断试图从外部来限
制国家理由(Foucault,2008a:10; 福柯,2018a:14)。
其次,在这个大前提下,治理必然僭越法律,管治是“国王以非法律
的形式直接对其臣民采取的行动……管治因此而存在于王权对作为臣
民的个人的主权者操演中。 换言之,管治是主权者以主权之名的直接治
理术”( Foucault,2007:340; 福柯,2010:304-305),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
理解。一是中央集权的治理权力对封建司法的凌驾甚至架空。如上文所
述,中世纪后期到 17 世纪,司法机构是封建的,是地方力量谋私体系的
一 部 分 , 经 常 逃 避 王 室 权 力 的 镇 压 命 令 ( Foucault,2015:123; 福 柯 ,
2016:112)。 行政国家的目的之一就是跳出这一限制,自主地预防和镇
压叛乱,因此,国家的专门镇压部门“给了自己颠覆基本司法规则的权
利”(Foucault,2019:86; 福柯,2019:119)。 事实上,它的确“剥夺了很多
人的司法权力,并因此也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力,尤其是消除了剩余的
封建要素和议员”(Foucault,2015:125; 福柯,2016:113)。二是国家层面
的治理对法律的僭越。 17 世纪后期以来建立的国家行政机构都有跨坐
在司法和非司法之上的典型特征:司法总督、管治总督和财政总督同时
是行政的和准司法的(parajudicial);管治副官和总督至少在某些案例中
拥有干预并替代常规的司法机器、 代表司法体系做出适当的司法决定
的权利,譬如在一些流浪者案例中,管治总督有权做出司法判决;副官
和总督们不需要考察任何司法形式,也不需要做出司法意义上的决定,
·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