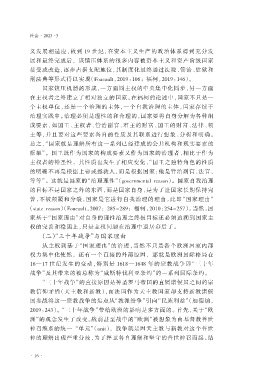Page 23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23
社会·2023·3
义发展相适应,故到 19 世纪,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政治体系得到充分发
展和最终完成后, 该镇压体系的很多内容被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
接受或改造,逐步占据支配地位,其制度化最终通过法院、管治、监狱和
刑法典等形式得以实现( Foucault,2019:106; 福柯,2019:146)。
国家镇压机器的形成,一方面同主权的中央集中化同步,另一方面
在主权者之外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国家。 在福柯的论述中,国家不只是一
个主权单位,还是一个治理的主体,一个自我治理的主体,国家存续于
治理实践中。 治理必须是理性的和合理的,国家要将自身分解为各种组
成要素,如国王、主权者、管治副官、君主的财富、国王的财富、法律、领
土等,并且要对这些要素各自的性质及其联系进行想象、分析和明确。
总之,“国家就是理解所有这一系列已经建成的公共机构和现实要素的
框架”。 国王既作为国家的构成要素又作为国家的治理者,相比于作为
主权者的神圣性, 其性质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国王之独特角色的性质
的明确不再是根据上帝或拯救人,而是根据国家:他是管治副官、法官,
等等”。 这就是国家的“治理理性”( governmental reason)。 国家自我治理
的目标不是国家之外的东西,而是国家自身,是为了让国家长期保持完
善,不被颠覆和分裂,国家是它进行自我治理的理由,此即“国家理由”
( state reason)(Foucault,2007: 285-289; 福柯,2010:254-257)。 当然,国
家基于“国家理由”对自身的理性治理之终极目标还必须追溯到国家主
权的完善和稳固上,只是主权问题在治理中退居幕后了。
(二)“三十年战争”与国家理由
从主权到基于“国家理由”的治理,当然不只是各个欧洲国家内部
权力集中化使然, 还有一个直接的外部原因, 那就是欧洲国际格局在
16—17 世纪发生的变动,特别是 1618—1648 年的宗教战争即“三十年
战争”及其带来的被总称为“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一系列国际条约。
“ 三十年战争”的直接原因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直属诸侯国之间的宗
教信仰矛盾(天主教和新教),而法国作为天主教国家却支持新教诸侯
国参战将这一宗教战争的焦点从“教派纷争”引向“民族利益”(加德纳,
2019:243)。“三十年战争”带给欧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关于“欧
洲”的观念发生了改变。战前甚至战中的“欧洲”被想象为由基督教普世
神召维系的统一“单元”(unit), 战争就是因天主教与新教对这个普世
神的理解出现严重分歧,为了捍卫各自理解和坚守的普世神召而起。 结
·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