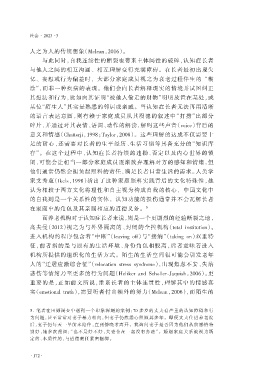Page 179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179
社会·2023·3
人之为人的传统想象(Mclean,2016)。
与此同时,自我连续性的断裂也带来主体间性的破碎,认知症长者
与他人之间的相互沟通、 相互理解变得充满障碍。 在长者最初出现失
忆、 妄想或行为偏差时, 大部分家庭成员视之为衰老过程伴生的“糊
涂”,而非一种疾病的表现。 他们会向长者解释现实的情境并试图纠正
其想法和行为,比如向其证明“被他人偷走的财物”明明放置在某处,或
某位“陌生人”其实是熟悉的邻居或亲戚。 当认知症长者无法再用清晰
的语言表达意图,则有赖于家庭成员从其漫漶的叙述中“打捞”出部分
碎片,并通过对其表情、语调、动作的解读,解码这些声音( voice)背后的
意义和情感(Chatterji,1998;Taylor,2008)。 这些理解的达成不仅需要十
足的耐心,还需要对长者的生平经历、生活习惯等具备充分的“知识库
存”。 在这个过程中,认知症长者持续的违拗、否定以及内心世界的锁
闭,可能会让相当一部分家庭成员逐渐放弃理解对方的感知和情绪,但
他们通常仍然会担负起照料的责任,满足长者日常生活的需求。 人类学
家艾秀慈(Ikels,1998)指出了这种家庭照料实践背后的文化特殊性,她
认为相较于西方文化将理性和自主视为构成自我的核心, 中国文化中
的自我则是一个关系性的实体, 认知功能的损伤通常并不会瓦解长者
在家庭中的角色及其亲属相应的道德义务。 5
而养老机构对于认知症长者来说,则是一个更剧烈的经验断裂之地,
高夫曼(2012)视之为与外界隔离的、封闭的全控机构(total institution)。
进入机构的程序包含着“中断”(leaving off)与“接纳”(taking on)双重特
征,前者指的是与原有的生活环境、身份角色相脱离,后者意味着进入
机构所提供的组织化的生活方式。 陌生的生活空间很可能会引发老年
人的“迁居应激综合征”(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出现焦虑不安、失落
悲伤等情绪乃至更多的行为问题(Heliker and Scholler鄄Jaquish,2006)。更
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说,维系长者的主体连贯性,理解其中的情感真
实(emotional truth),需要听者付出额外的努力(Mclean,2006),而陌生的
5.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遇到一个印象深刻的案例:70 多岁的丈夫有严重的认知障碍和行
为问题,甚至常常对妻子暴力相向,但妻子仍然悉心照顾其多年。 即便丈夫住进养老院
后,妻子仍每天一早前来陪伴,直到傍晚才离开。 我询问妻子是否因为他们从前感情特
别好,她多次强调:“也不是好不好,夫妻合在一起没有办法”。 婚姻家庭 关系被 视为既
定的、本质性的,与道德责任紧密捆绑。
· 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