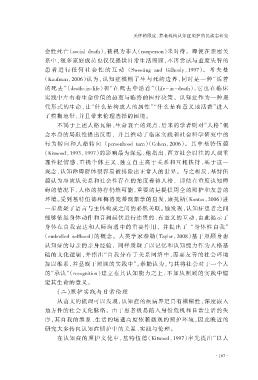Page 174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174
关怀的限度:养老机构认知症照护的民族志研究
会性死亡(social death),被视为非人(nonperson)来对待。 即便在亲密关
系中,很多家庭成员也仅仅提供日常生活照顾,不再尝试与重度失智的
患 者 进 行 任 何 社 会 性 的 互 动 (Sweeting and Gilhooly,1997)。 考 夫 曼
( Kaufman,2006)认为,认知症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同时是一种“活着
的死去”(death鄄in鄄life)和“在死去中活着”(life-in-death),它 也 在临 床
实践中左右着生命价值的协商与临终的医疗决策。 认知症作为一种现
代形式的生命,让“什么是构成人的属性”“什么是有意义地活着”进入
了模糊地带,并且带来伦理选择的困境。
不同于上述人格瓦解、生命衰亡的观点,后来的学者则对“人格”概
念本身的局限性提出反思, 并且推动了临床实践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
行为转向和人格转向 ( personhood turn)(Cohen,2006)。 其 中 基 特 伍 德
( Kitwood,1993,1997)的影响最为深远,他指出,西方社会以往的人观重
理性轻情感,重视个体主义、独立自主高于关系和互相扶持,基于这一
观念,认知障碍群体很容易被排除出正常人的世界。 与之相反,基特伍
德认为应该从关系和社会性存在的角度看待人格, 即使在重度认知障
碍的情况下,人格的持存仍然可能,重要的是提供周全的照护和友善的
环境。受到基特伍德和梅洛庞蒂现象学的启发,康托斯(Kontos,2006)进
一步质疑了语言与主体构成之间的必然关联。 她发现,认知症患者之间
能够依靠身体动作和音调起伏进行连贯的、有意义的互动,由此揭示了
身体在自我表达和人际沟通中的重要作用, 并提出了“身体性自我”
( embodied selfhood)的概念。 人类学家泰勒(Taylor,2008)基于照顾身患
认知症的母亲的亲身经验, 同样质疑了以记忆和认知能力作为人格基
础的文化逻辑,并指出“自我分布于关系网络中,需要友善的社会环境
加以维系,并显现于照顾的实践中”。泰勒认为,与其将社会对于一个人
的“承认”(recognition)建立在其认知能力之上,不如从照顾的实践中锚
定其生命的意义。
(二)照护实践与日常伦理
从前文的梳理可以发现,认知症的疾病界定具有模糊性,深度嵌入
地方性的社会文化脉络。 由于患者极易陷入身份危机和日常生活的失
序,其自我的维系、生活的境遇高度依赖微观的照护环境,因此晚近的
研究大多转向认知症照护中的关系、实践与伦理。
在认知症的照护文化中,基特伍德(Kitwood,1997)率先提出“以人
· 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