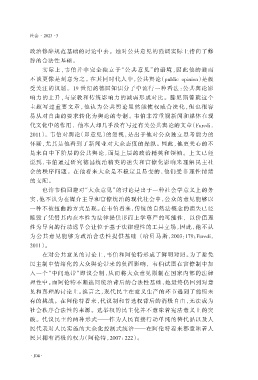Page 111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111
社会·2023·3
政治修辞规范基础的讨论中去。 她对公共意见的强调实际上指向了修
辞的合法性基础。
实际上,韦伯并非完全独立于“公共意见”的语境,因此他的避而
不谈更像是刻意为之。 在其同时代人中,公共舆论( public opinion)是极
受关注的议题。 19 世纪的德国知识分子中流行一种看法:公共舆论影
响力的上升,与宗教和传统影响力的减弱形成对比。 滕尼斯曾就这个
主题写过重要文章,他认为公共舆论虽然能使权威合法化,但也很容
易从对自由的要求转化为舆论的专制。 韦伯非常重视新闻和媒体在现
代文化中的作用, 他本人却几乎没有写过有关公共舆论的文章( Furedi,
2011)。 韦伯对舆论(即意见)的忽视,是出于他对公众独立思考能力的
怀疑,尤其是他看到了新闻业对大众态度的操纵。 因此,他更关心的不
是来自中下阶层的公共舆论,而是上层的政治精英和领袖。 上文已经
说到,韦伯通过研究德国统治精英的迷失和官僚化影响来理解民主社
会的秩序问题。 在他看来大众是不稳定且易变的,他们受非理性情绪
的支配。
也许韦伯回避对“大众意见”的讨论是出于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务
实,他不认为在媒介主导和官僚统治的现代社会中,公众的意见能够以
一种不被扭曲的方式呈现。 在韦伯看来,传统的自然法概念的消失已经
摧毁了凭借其内在本性为法律提供形而上学尊严的可能性, 以价值理
性为导向的行动迟早会让位于基于法律理性的工具立场,因此,他不认
为 公共意见能够为政治合法性提供基础 (哈贝马斯,2003:179;Furedi,
2011)。
在对公共意见的讨论上,韦伯和阿伦特形成了鲜明对照。为了避免
民主制中情绪化的大众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 韦伯试图在官僚制中加
入一个“中间地带”即议会制,从而将大众意见限制在国家内部的法律
理性中。 而阿伦特不断追问统治背后的合法性基础,她最终仍回到对意
见和真理的讨论上。 换言之,现代民主在意义生产的环节遇到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 在阿伦特看来,代议制和普选权背后的消极自由,无法成为
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来源。 选举权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宪法意义上的突
破。 代议民主的两种形式———作为人民直接行动单纯的替代品以及人
民代表对人民实施的大众化控制式统治———在阿伦特看来都意味着人
民只拥有消极的权力(阿伦特,2007:222)。
·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