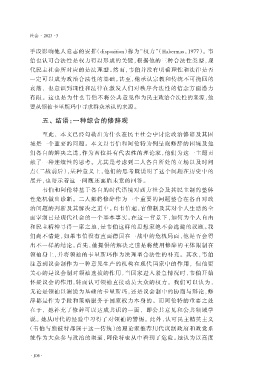Page 113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113
社会·2023·3
手段影响他人意志的安排(disposition)称为“权力”(Habermas,1977)。 韦
伯也认可合法性是权力得以形成的关键,根据他的三种合法性类型,现
代民主社会所对应的是法理型。 然而,韦伯并没有明确理性和法律是否
一定可以成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甚至,他承认宗教和传统不可挽回的
衰落, 也意识到理性和法律在激发人们对秩序合法性的信念方面潜力
有限。 这也是为什么韦伯不将公共意见作为民主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他
要从领袖卡里斯玛中寻求群众承认的来源。
五、 结语:一种综合的修辞观
至此, 本文已经勾勒出为什么在民主社会中讨论政治修辞及其困
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文以韦伯和阿伦特为例呈现修辞的困境及他
们各自的解决之道,作为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们为这一主题贡
献了一种连续性的思考。 尤其是考虑到二人各自所处的立场以及时间
点(二战前后),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思考既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历史中的
展开,也暗示着这一问题还面临未竟的回答。
韦伯和阿伦特基于各自的时代语境对西方社会及其民主制的整体
性危机做出诊断。 二人都将修辞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整合在各自对政
治问题的判断及其解决之道中。 自韦伯起,官僚制及其对个人生活的全
面宰制已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为个人自由
和民主精神寻得一席之地,是韦伯这样的思想家绝不会逃避的议题。 我
们尚不清楚,如果韦伯没有直面德国在一战中的危机局面,他是否会得
出不一样的结论。 首先,他提供的解决之道是将使用修辞的主体限制在
领袖身上,并将领袖的卡里斯玛作为法理型合法性的补充。 其次,韦伯
注意到议会制作为一种意见生产的机构在现代国家中的作用, 但他更
关心的是议会制对领袖选拔的作用,当国家进入紧急情况时,韦伯开始
怀疑议会的作用,转而认可领袖直接动员大众的权力。 我们可以认为,
无论是领袖以演说为基础的卡里斯玛,还是议会制中的协商与辩论,修
辞都是作为手段和策略服务于国家权力本身的。 而阿伦特的重要之处
在于, 她补充了修辞可以达成共识的一面, 即公共意见和公共领域学
说。 她从时代的经验中习得了对领袖的警惕。 此外,认可民主精英主义
(韦伯与熊彼特都属于这一传统)的理论家推荐用代议制政府和政党系
统作为大众参与政治的渠道,阿伦特也从中看到了危险。 她认为以高度
· 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