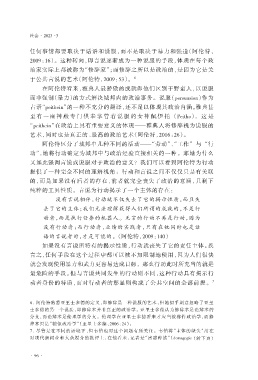Page 103 - 《社会》2023年第3期
P. 103
社会·2023·3
任何事情都要取决于话语和说服,而不是取决于暴力和强迫(阿伦特,
2009:16)。 这种转向,即言说逐渐成为一种说服的手段,体现在每个政
治家实际上都被称为“修辞家”;而修辞之所以是政治的,是因为它是关
于公共言说的艺术(阿伦特,2009:53)。 6
在阿伦特看来,雅典人最骄傲的成就即他们区别于野蛮人,以说服
而非强制(暴力)的方式解决城邦内的政治事务。 说服(persuasion)作为
古语“ peithein”的一种不充分的翻译,还不足以体现其政治内涵。雅典甚
至 有 一 座 神 殿 专 门 供 奉 掌 管 着 说 服 的 女 神 佩 伊 托 ( Peitho), 这 是
“ peithein”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体现———雅典人将修辞视为说服的
艺术,同时也是真正的、最高的政治艺术(阿伦特,2016:26)。
阿伦特区分了城邦中几种不同的活动———“劳动”、“工作” 与“行
动”,她将行动确定为城邦中与政治经验直接相关的一种。 那她为什么
又如此强调言说或说服对于政治的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为行动
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视角: 行动和言说之间不仅仅只是有关联
的,而是如果没有后者的存在,前者就完全丧失了政治的意涵,只剩下
纯粹的工具性质。 言说为行动揭示了一个主体的存在:
没有言说相伴,行动就不仅失去了它的揭示性质,而且失
去了它的主体;我们无法理解获得人们所谓的成就的,不是行
动者,而是执行任务的机器人。 无言的行动不再是行动,因为
没有行动者;而行动者,业绩的实践者,只有在他同时也是话
语的言说者时,才是可能的。 (阿伦特,2009:140)
如果没有言说所特有的揭示性质,行动就丧失了它的责任主体。 换
言之,任何手段在这个过程中都可以被不加限制地使用,因为人们很快
就会发现使用暴力和武力更容易达成目标, 那么行动此时所充当的就是
最危险的手段。 但与言说共同发生的行动则不同,这种行动具有揭示行
动者身份的特质,而对行动者的彰显则构成了公共空间的全部前提。 7
6. 阿伦特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即修辞是一种说服的艺术,但她似乎刻意忽略了亚里
士多德的另一个说法,即修辞术并非真正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是论辩术的
分支,而论辩术是伦理学的分支。 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才应当被称作政治学,而修
辞术只是“ 貌似政治学”(亚里士多德,2006:24)。
7. 尽管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但韦伯也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 韦伯将“主体的缺失”用 在
对现代新闻业和大众媒介的批评上,在他看来,记者是“蛊惑种族”(demagogic(转下页)
·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