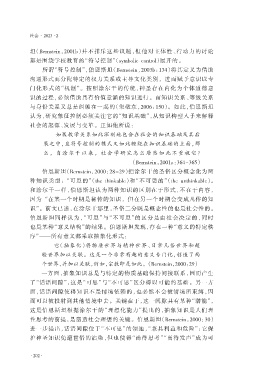Page 209 - 《社会》2023年第2期
P. 209
社会·2023·2
坦(Bernstein,2001b)并不排斥这些议题,但他对主体性、行动力的讨论
都是围绕学校教育的“符号控制”(symbolic control)展开的。
所谓“符号控制”,伯恩斯坦(Bernstein,2003b:134)将其定义为借助
沟通形式而分配特定的权力关系或主导文化类别, 进而赋予意识以专
门化形式的“机制”。 按照涂尔干的传统,神圣存在内化为个体道德意
识的过程,必须借助具有价值意涵的知识进行。 而知识关系、等级关系
与身份关系又总是纠缠在一起的(渠敬东,2006:150)。 如此,伯恩斯坦
认为,研究象征控制必须关注它的“知识基础”,从知识构型入手来解释
社会的起源、发展与变革。 正如他所说:
如果教学关系如此深刻地包含在社会的知识基础及其后
果之中,且符号控制的模式又如此缠绕在知识基础的上面,那
么 , 自 涂尔 干 以 来 , 社 会 学 研 究 怎 么 居 然 如 此 不 重 视 它 ?
( Bernstein,2001a:364-365)
伯恩斯坦(Bernstein,2000:28-29)把涂尔干的圣俗区分概念化为两
种知识类型:“可思的”(the thinkable)和“不可思的”(the unthinkable)。
和涂尔干一样,伯恩斯坦认为两种知识的区别在于形式,不在于内容,
因为“在某一个时期是秘传的知识, 但在另一个时期会变成凡俗的知
识”。 前文已述,在涂尔干那里,圣俗二分既是概念性的也是社会性的。
伯恩斯坦同样认为,“可思”与“不可思”的区分是由社会决定的,同时
也是某种“意义结构”的结果。 伯恩斯坦发现,存在一种“意义的特定秩
—
序”——所有意义都采取抽象化形式:
它(抽象化)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日常凡俗世界和超
验世界加以关联。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意义专门化,创造了两
个世界,并加以关联,例如,宗教即是如此。 ( Bernstein,2000:29)
一方面,抽象知识总是与特定的物质基础保持间接联系,因而产生
了“话语间隙”,这是“可思”与“不可思”区分得以可能的基础。 另一方
面,话语间隙使得知识不是情境依赖的,也必然不会被情境所束缚,因
而可以被投射到其他情境中去。 关键在于,这一间隙具有某种“ 潜能”,
这是伯恩斯坦根据涂尔干的“理想化能力”提出的,抽象知识是人们理
性思考的前提,是塑造社会理想的关键。 伯恩斯坦(Bernstein,2000:30)
进一步提出,话语间隙位于“不可思”的领地,“兼具利益和危险”:它保
护神圣知识免遭世俗的沾染,但也使得“尚待思考”“尚待发声”成为可
· 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