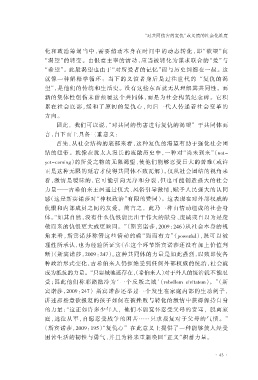Page 50 - 《社会》2023年第1期
P. 50
“对共同伤害的复仇”或义愤的社会化维度
化和政治筹划当中,需要情动本身在时间中的动态转化,即“欲望”向
“渴望”的转变。 由恨意主宰的情动,应当被转化为谋求联合的“爱”与
“希望”。 此般渴望也由于“对所爱者的记忆”而与历史纠缠在一起。 这
就像一种解释学循环: 当下的义愤者 身后 是 过 往 世 代 的“复仇的渴
望”,是他们的传统和生活史。 没有这些东西就无从理解其共同性。 而
新的集体性创伤未曾颠覆这个共同体,而是为社会构筑纪念碑。 它积
累在社会底部,缓和了原初的复仇心,向后一代人传递着社会变革的
方向。
因此, 我们可以说,“对共同的伤害进行复仇的渴望” 于共同体而
言,自下而上具备三重意义:
首先,从社会结构的底部来看,这种复仇的渴望有助于强化社会团
结的纽带。 就像在犹太人漫长的流散历史中,一种对“尚未到来”( not-
yet-coming)的所爱之物的无限渴望,使他们能够忍受巨大的苦难(或许
正是这种无限的延宕才使得共同体不致瓦解)。 仅从社会团结的视角来
看,激情是暧昧的,它可能引向无序和分裂,但也可能创造强大的社会
—
力量——古希伯来王国通过仪式、风俗引导激情,赋予人民强大的认同
感(这是斯宾诺莎对“神权政治”有限的赞同)。 这表现在对外部权威的
仇恨和内部成员之间的友爱。 简言之, 此乃一种由情动组成的社会身
体。“ 如其自然,没有什么仇恨能比出于伟大的献身、虔诚或自以为是虔
敬而来的仇恨更大或更顽固。 ”(斯宾诺莎,2009:246)从社会本身的视
角来看,斯宾诺莎称赞这些情动的确“强而有力”(powerful),既可以被
理性所承认,也为经验所证实(在这个环节斯宾诺莎还没有加上价值判
断)(斯宾诺莎,2009:247)。这种共同体的力量是如此强烈,以致即使各
种政治形式变化,古希伯来人仍拒绝受到任何外部权威的统治,社会就
成为抵抗的力量。“只要城池还存在,(希伯来人)对于外人的统治就不能忍
受;因此他们称耶路撒冷为‘一个反叛之城’(rebellem civitatem)。 ”(斯
宾诺莎,2009:247) 斯宾诺莎还举过一个发生在家庭内部的生动例子,
讲述那些意欲报复的孩子如何在被挫败与转化的激情中获得保持自身
的力量:“这正如许多少年人, 他们不能宽怀忍受父母的责骂, 脱离家
庭,逃往从军,自愿忍受战争的困苦……只求报复对于父母的气愤。 ”
(斯宾诺莎,2009:195)“复仇心” 在此意义上提供了一种能够使人经受
困苦生活的韧性与勇气,并且为将来重新唤回“正义”积蓄力量。
·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