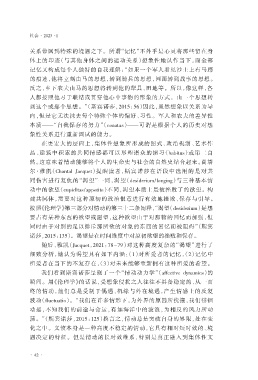Page 49 - 《社会》2023年第1期
P. 49
社会·2023·1
关系带回到特殊的境遇之下。 所谓“记忆”不外乎是心灵将那些留在身
体上的印迹(与其他身体之间的运动关系)想象性地认作当下,而全部
记忆又构成每个人独特的自我理解:“如果一个军人看见沙土上有马蹄
的痕迹,他将立刻由马的思想,转到骑兵的思想,因而转到战事的思想。
反之,乡下农夫由马的思想将转到他的犁具、田地等。 所以,像这样,各
人都按照他习于联结或贯穿他心中事物的形象的方式, 由一个思想转
到这个或那个思想。 ”(斯宾诺莎,2015:56)因此,虽然想象以关系为导
向,但是它无法抹去每个特殊个体的偏好、习性。 军人和农夫的差异性
本质——
—“自我保存的努力”(conatus)———可谓是根据个人的历史对想
象性关系进行重新调试的能力。
在更宏大的层面上,集体性想象所形成的图式、政治机制、艺术作
品、建筑中积累的共同情感都可以形塑诸众的惯习( habitus)或第二自
然。这意味着情动能够将个人的生命史与社会的自然史结合起来。尚塔
尔·雅凯( Chantal Jacquet)提醒读者,斯宾诺莎在语 段 中 选用 的是对 共
同伤害进行复仇的“渴望”一词,渴望(desiderium/longing)与三种基本情
动中的欲望(cupiditas/appetite)不同,渴望本质上是被挫败了的欲望。 构
建共同体,需要对这种原初的政治恨意进行有效地挫败、保存与引导。
按照《伦理学》第三部分对情动的第三十二条阐释,“渴望(desiderium)是想
要占有某种东西的欲望或愿望,这种欲望由于对那物的回忆而加强,但
同时由于对别的足以排斥那所欲的对象的东西的回忆而被阻碍”(斯宾
诺莎,2015:135)。 渴望是在时间维度中对原初欲望的挫败和保存。
随后,雅凯(Jacquet,2021:78-79)对这种高度复杂的“渴望”进行了
细致分析,她认为渴望具有如下内涵:(1)对所爱者的记忆,(2)记忆中
所爱者在当下的不复存在,(3)对未来能够重新拥有这种所爱的希望。
我们看到斯宾诺莎呈现了一个“情动动力学”(affective dynamics)的
瞬间。 用《伦理学》的话说,受想象侵扰之人往往不具备稳定的、从一而
终的情动,他们总是受制于偶遇、机缘与外在境遇,产生情感上的反复
波动(fluctuatio)。“我们在许多情形下,为外界的原因所扰攘,我们徘徊
动摇,不知我们的前途与命运,有如海洋中的波浪,为相反的风力所动
荡。 ”(斯宾诺莎,2015:125)换言之,情动总是突破自身的界限,处在变
化之中。 义愤本身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情动,它具有相对短时效的、境
遇决定的特征。 但是情动的长时效维系,特别是真正融入到集体性文
·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