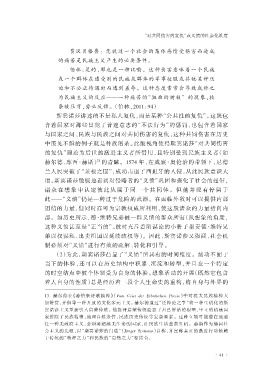Page 48 - 《社会》2023年第1期
P. 48
“对共同伤害的复仇”或义愤的社会化维度
贾汉贝格鲁: 您说过一个社会的集体感情受伤害而造成
的痛苦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必要条件。
伯林:是的,那也是一种比喻。 这种伤害意味着一个民族
或一个群体在遭受别的民族或群体的军事征服或其他某种压
迫和不公正待遇时而遭到羞辱。 这种态度常常会导致我称之
为民族主义的反应——一种痛苦的“扭曲的树枝” 的现象,枝
—
条被压弯,势必反弹。 (伯林,2011:94)
斯宾诺莎讲述的不是私人复仇,而是某种“公共性的复仇”。 这既包
含着国家对那些冒犯了普遍意志的“不法行为”的惩罚,也包含着国家
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对共同伤害的复仇,这种共同伤害在历史
中屡见不鲜的例子就是种族屠杀。 此般视角使得斯宾诺莎“对共同伤害
的复仇”理论为后世的激进主义者所借用,且特别受到民族主义者(如
13
赫尔德、摩西·赫斯) 的青睐。 1574 年,在威廉·奥伦治的带领下,尼德
兰人民突破了“莱顿之围”,成功击退了西班牙的入侵,从此民族意识大
增。斯宾诺莎敏锐地看到对侵略者的“义愤”巩固和强化了社会的纽带,
诸 众 在 想 象 中 认 定 彼 此 从 属 于 同 一 个 共 同 体 。 但 他 并 没 有 停 留 于
此———“义愤”仍是一种过于危险的武器。 在面临外敌时可以提供内部
团结的力量,但同时亦可为宗教权威所利用,使这股诸众的力量指向内
部。 如历史所示,德·维特兄弟被一群义愤的群众所害(从想象的角度,
这种义愤甚至是“正当的”。彼时充斥着阴谋论的小册子指责德·维特兄
弟以权谋私、出卖祖国以延续政权等)。 因此,斯宾诺莎又强调,社会机
制必须对“义愤”进行有效的疏解、转化和引导。
( 2)为此,斯宾诺莎凸显了“义愤”所具有的时间维度。 情动不囿于
当下的体验,还可以在历史结构中积累、沉淀和转型,并且在一个特定
的时空结点中被个体领受为自身的体验。 想象活动的开展(既然它包含
着人自身的性质)总是经历着一段个人生命史的重构,将自身与外界的
13. 赫尔德在《希伯来诗歌精神》(Vom Geist der Erbr覿schen Poesie)中对犹太民族精神大
加赞赏,并倡导一种开放的文化多元主义。 赫尔德通过“泛神论之争”将一种生机化的斯
宾诺莎主义重新引入启蒙传统。 他批评启蒙传统遗忘了自己鲜活的根基,中立的机械国
家排除了民族精神、地理自然条件、民族历史传统等复杂要素。 这种立场可能潜在地通
往一种无政府主义,必须要超越无生命的国家,让民族生活重获生机。 赫斯作为德国社
会主义的先驱,以“斯宾诺莎的门徒”( Jünger Spinozas)自称,并宣称真正的激进行动依赖
于传统的“精神之力”和民族的“自然之力”相结合。
·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