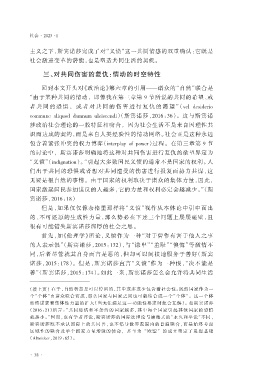Page 45 - 《社会》2023年第1期
P. 45
社会·2023·1
主义之下,斯宾诺莎完成了对“义愤”这一共同情感的双重确认:它既是
社会激进变革的潜能,也是塑造共同生活的契机。
三、对共同伤害的复仇:情动的时空特性
回到本文开头对《政治论》第六章的引用———诸众的“自然”联合是
“由于某种共同的情动, 即像我在第三章第 9 节所说的共同的希望、或
者 共 同 的 恐 惧 , 或 者 对 共 同 的 伤 害 进 行 复 仇 的 渴 望 ”(vel desiderio
commune aliquod damnum ulciscendi)(斯宾诺莎,2016:36)。 这与斯宾诺
莎政治社会理论的一般特征相吻合, 因为社会生活不是来自因理性共
识而达成的契约,而是来自人类经验性的情动网络。 社会正是这种永远
包含着紧张冲突的权力博弈(interplay of power)过程。 在第三章第 9 节
的讨论中, 斯宾诺莎明确地将这种对共同伤害进行复仇的欲望界定为
“义愤”( indignation)。“引起大多数国民义愤的通常不是国家的权利。 人
们出于共同的恐惧或者想对共同遭受的伤害进行报复而协力共谋,这
无疑是很自然的事情。 由于国家的权利取决于诸众的集体力量,因此,
国家激起国民参加谋反的人越多,它的力量和权利必定会越减少。”(斯
宾诺莎,2016:18)
但是,如果仅仅像奈格里那样将“义愤”视作从本体论中引申而出
的、不可还原的生成性力量,那么势必在下述三个问题上屡屡碰壁,且
很有可能错失斯宾诺莎深厚的社会之思。
首先,如《伦理学》所论,义愤作为一种“对于曾作有害于他人之事
的人表示恨”(斯宾诺莎,2015:132),与“谦卑”“羞耻”“懊悔”等激情不
同,后者尽管就其自身而言是恶的,但却可以间接地服务于善好(斯宾
诺莎,2015:178)。 但是,斯宾诺莎直言“义愤”作为一种恨,“决不能是
善”(斯宾诺莎,2015:174)。 如此一来,斯宾诺莎怎么会允许将共同生活
(接上页) 在于,自然状态是可以停留的,其中或多或少包含着社会性。既然国家作为一
个“个体”由诸众联合而成,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可能结合成一个“个体”。 这一个体
始终谋求着集体性力量的扩大(当无法满足这一功能性要求时便会瓦解)。 如斯宾诺莎
( 2016:21)所言:“共同 缔结和 平条约 的国家 越多,其 中每个 国家引 起其他 国家的 恐 惧
就越小。 ”因而,也有学者评论,斯宾诺莎的国际法理论与康德式的“永久和平论”不同,
斯宾诺莎 既不承 认国际 上的共 同善,也 不倡导 世界范 围内的 普遍联 合,而是始 终 考 虑
区域性 的联合 及单个 国家力 量增强 的使命 , 甚 至 为 “欧 盟 ” 的 成 立 奠 定 了 思 想 基 础
( Altwicker,2019:65)。
·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