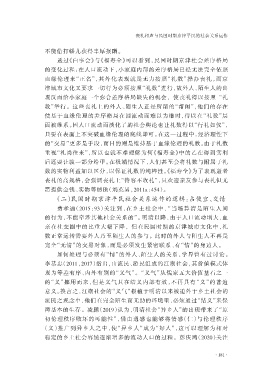Page 188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188
丧礼相声与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的社会关系运作
不能借打幡儿获得丰厚报酬。
透过《白事会》与《福寿全》可以看到,民国时期京津社会差序格局
的变化过程:在人口流动下,小家庭内部的差序格局已经无法完全依照
血缘伦理来“正名”,其外化表现就是无力按照“礼数”操办丧礼,而京
津城市文化又要求一切行为必须按照“礼数”进行,故外人、陌生人的出
现反而给小家庭一个弥合差序格局缺失的机会, 使丧礼得以按照“礼
数”举行。 这些丧礼上的外人、陌生人正是所谓的“帮闲”,他们的存在
使基于血缘伦理的差序格局在因流动而难以为继时,得以在“礼数”层
面被维系。因人口流动而淡化了的社会舆论也让礼数得以“行礼如仪”,
只要在表面上不突破血缘伦理的底线即可。 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理性下
的“交易”更多是手段,而目的则是维持基于血缘伦理的礼数。由于礼数
重视“礼尚往来”,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福寿全》中的乙在得到实利
后还要让渡一部分给甲。 在极端情况下,人们甚至会将礼数与附属于礼
数的实物利益加以区分,以保证礼数的纯粹性。《福寿全》为了表现逝者
丧礼的高规格,会强调丧礼上“待客不收礼”,只欢迎亲友参与丧礼但无
需提供金钱、实物等赙助(刘英男,2011a:454)。
(二)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社会关系运作的逻辑:占便宜、交情
费孝通(2015:93)关注到,在乡土社会中,“当 场 算 清是 陌 生 人 间
的行为,不能牵涉其他社会关系的”。 明清以降,由于人口流动增大,血
亲在社交圈中的比重大幅下降, 但在民国时期的京津城市文化中,礼
数正常运转需要外人乃至陌生人的参与。 此时的外人与陌生人不再是
完全“无情”的交易对象,而是必须发生紧密联系、有“情”的身边人。
如何处理与必须有“情”的外人、陌生人的关系,学界曾有过讨论。
李恭忠(2011,2017)指出,由流民、游民组成的江湖社会,其价值模式体
现为等差有序、内外有别的“义气”。“义气”从儒家五大价值基石之一
的“ 义”挪用而来,但是义气只在结义内部有效,不再具有“义”的普遍
意义。换言之,江湖社会的“义气”根植于明清以来被迫外于乡土社会的
流民之观念中,他们在完全陌生而无助的环境里,必须通过“结义”来保
障基本的生存。 凌鹏(2019)认为,明清社会“异乡人”的出现带来了“原
初伦理秩序败坏的可能性”,借由通感也能够将情感(仁)与伦理秩序
(义)推广到异乡人之中,使“异乡人”成为“好人”,这可以理解为相对
稳定的乡土社会容纳逐渐增多的流动人口的过程。 彭庆鸿(2020)关注
· 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