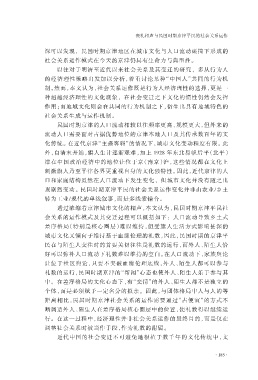Page 192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192
丧礼相声与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的社会关系运作
深可以发现, 民国时期京津地区在城市文化与人口流动碰撞下形成的
社会关系运作模式在今天的京津仍具有生命力与典型性。
以往对于明清至近代以来社会关系及其变迁的研究, 多从行为人
的经济理性策略出发加以分析,着重讨论某种“中国人”共同的行为机
制。然而,本文认为,社会关系运作既是行为人经济理性的选择,更是一
种超越经济理性的文化现象, 在社会变迁之下文化的惯性仍然会发挥
作用;而地域文化则会在共同的行为机制之下,衍生出具有地域特色的
社会关系生成与运作机制。
民国时期京津的人口流动相较以往频率更高、规模更大,但外来的
流动人口需要面对占据优势地位的京津本地人口及其传承数百年的文
化传统。 在近代京津“主强客弱”的情况下,城市文化变动程度有限。 此
外,自清末开始,旗人生计逐渐艰难,加上 1928 年东北易帜后平(北平)
津在中国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让位于京(南京)沪,这些情况都在文化上
刺激旗人乃至平津各界更重视自身的文化独特性。 因此,近代京津的人
口和家庭结构虽然在人口流动下发生变化, 但城市文化并没有随之出
现剧烈变动。 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的社会关系运作变化并非由农业/乡土
转为工业/现代的单线叙事,而是多线索错合。
透过浓缩着京津城市文化的相声,本文认为,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社
会关系的运作模式及其变迁过程可以概括如下: 人口流动导致乡土式
差序格局(特别是核心圈层)难以维持,但受旗人生活方式影响甚深的
城市文化又倾向于维持基于血缘伦理的礼数,因此,民国时期的京津平
民在与陌生人交往时的首要关切往往是礼数的运行,而外人、陌生人恰
好可以弥补人口流动下礼数难以维持的空白。 在人口流动下,家族舆论
让位于社区舆论,只要不突破血缘伦理底线,外人、陌生人都可以参与
礼数的运行,民国时期京津的“帮闲”心态也使外人、陌生人乐于参与其
中。 在差序格局的文化心态下,有“交情”的外人、陌生人都不是独立的
个体,而是必须赋予一定名分的拟亲。 因此,与团体格局中人与人的等
距离相比,民国时期京津社会关系的运作需要通过“占便宜”的方式不
断调适外人、陌生人在差序格局核心圈层中的位置,使礼数得以继续运
行。 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理性并非社会关系运作的最终目的,而是仅在
调整社会关系时被当作手段,作为礼数的附属。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不可避免地根植于数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文
· 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