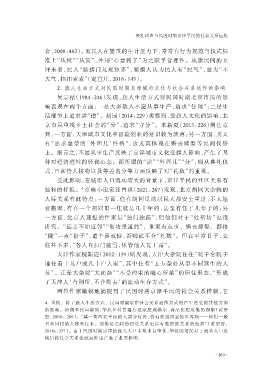Page 176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176
丧礼相声与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的社会关系运作
舍,2008:462)。 而民人在繁重的生计压力下,常常在行为规范与仪式标
准上“从权”“从简”,并用“心意到了”为之赋予合理性。 从旗民间的互
评来看,民人“嫌旗门儿规矩多”,而旗人认为民人有“民气”,意为“不
大气,扣扣索索”(定宜庄,2016:145)。
2. 旗人生活方式对民国时期京津城市文化与社会关系运作的影响
吴宗祜(1984:246)发现,旗人生活方式对民国时期北京市民的影
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多数人不愿从事生产,追求“住闲”;二是生
活细节上追求讲“谱”。 赵园(2014:229)观察到,受旗人文化的影响,北
京市民重视乡土社会的“分”,追求“守分”。 来新夏( 2013:226)则注意
到,一方面,天津城市文化中冒险创业的意识较为淡薄;另一方面,其又
有“追 求 虚 荣 的‘外 面 儿 ’性 格 ”,这 尤 其 体 现 在 婚 丧 嫁 娶 等 民 间 仪 俗
上。 细言之,不愿从事生产反映了京津城市文化受旗人影响,产生了某
种对经济理性的轻视心态。 而所谓的“谱”“外面儿”“分”,则从典礼仪
式、日常待人接物以及等差名分等方面反映了对“礼数”的重视。
受此影响,在城市人口流动增大的背景下,京津平民的社区关系有
独特的样貌。 4 京味小说家汪曾祺(2021:267)发现,北京胡同大杂院的
人际关系有此特点:一方面,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
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就是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另
一方面,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但他们对于“处街坊”也很
讲究。“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 谁家有点事, 婚丧嫁娶, 都得
“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恼,否则就不合“礼数”。 但在平常日子,交
往并不多,“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天津作家倪斯霆(2012:139)则发现,天津大杂院往往“院子套院子
地住着十几户或几十户人家”,其中住有“五方杂处从事不同营生的人
员”。 正是大杂院“大而杂”“不受约束的随心所欲”的居住形态,“形成
了天津人‘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流动生存方式”。
两位作家敏锐地捕捉到了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的社会关系样貌,它
4. 当然, 除了旗人生活方式, 民国时期京津社会关系运作方式的产生还受到其他方面
的影响。 清朝至民国期间,华北乡村普遍存在家庭规模小、商品化程度低的现象(黄宗
智,2014b:269)。“冀—鲁西北平原的大部分村民,仍有相当闭塞的世界观———他们一般
只和同村的人聊天往来。 而街坊之间的纽带关 系更富有准宗 族关系的色彩”(黄宗智,
2014a:257)。 由于民国时期京津的流入人口主要来自华北,华北的情况对于流动人口进
城后的社会关系生成运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 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