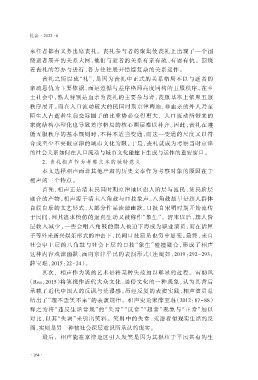Page 171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171
社会·2022·6
来往者都有义务出席丧礼。 丧礼参与者的聚集使丧礼上出现了一个围
绕逝者展开的关系大网,他们与逝者的关系有亲有疏、有恩有仇。 围绕
着丧礼的筹办与进行,各方往往展开错综复杂的关系运作。
丧礼之所以成“礼”,是因为丧礼中正式的关系格局不以与逝者的
亲疏恩仇为主要依据,而是遵循与差序格局高度同构的五服秩序。 在乡
土社会中,熟人特别是血亲为丧礼的主要参与者,丧服基本上依照五服
秩序展开。 而在人口流动较大的民国时期京津两地,非血亲的外人乃至
陌生人占逝者生前交际圈子的比重势必变得更大, 人口流动所带来的
家庭结构小型化也导致差序格局的核心圈层难以补齐。 因此,丧礼在遵
循五服秩序的基本规则时,不得不适当变通,而这一变通的尺度又以符
合或至少不突破京津的城市文化为限。 于是,丧礼就成为考察当时京津
的社会关系如何在人口流动与城市文化碰撞下生成与运作的重要窗口。
2. 丧礼相声作为考察文本的独特意义
本文选择相声而非其他严肃的历史文本作为考察对象的原因在于
相声的三个特点。
首先,相声正是清末民国时期京津地区旗人阶层与流民、贫民阶层
融合的产物。相声源于清末八角鼓与口技象声。八角鼓最早是旗人群体
自娱自乐的文艺形式,大部分作品诙谐幽默。 口技自宋明时期开始流传
于民间,因其追求模仿的逼真生动又被称作“象生”。 清末以后,旗人阶
层收入减少,一些会唱八角鼓的旗人被迫下海成为职业演员,而在话匣
子等外来新兴娱乐形式的冲击下,民间口技演员也穷中思变。最终,来自
社会中上层的八角鼓与社会下层的口技“象生”碰撞融合,形成了相声
这种内容戏谑幽默、面向京津平民的表演形式(连阔如,2019:292-293;
薛宝琨,2015:22-24)。
其次, 相声作为笑的艺术是将某种失范加以彰显的过程。 雷勤风
( Rea,2015)将笑视作近代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一种现象,认为其背后
承载了近代中国人的反讽与荒谬感。 历经反复的表演实践,相声演员总
结出了“理不歪笑不来”的表演规律。 相声史论家薛宝琨(2012:87-88)
释之为将“违反生活常规”的“失常”“反常”“超常”现象与“正常”加以
对比,以其“ 失调”来引出笑料。 笑料中的失常、荒谬看似现实生活的反
面,实则是另一种被社会深层意识所承认的现实。
最后, 相声能在京津地区引人发笑是因为其根植于平民共有的生
· 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