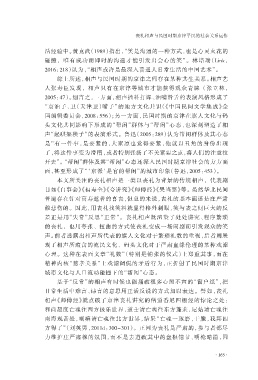Page 172 - 《社会》2022年第6期
P. 172
丧礼相声与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的社会关系运作
活经验中。黄克武(1989)指出,“笑是沟通的一种方式,也是心灵火花的
碰撞, 唯有成功而即时的沟通才能引发出会心的笑”。 林培瑞(Link,
2016:218)认为,“相声或许是最深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中国艺术”。
综上所述,相声与民国时期的京津之间存在某种共生关系。相声艺
人张寿臣发现, 相声只有在京津等城市才能获得观众青睐 (张立林,
2005:47)。细言之,一方面,相声插科打诨、油嘴滑舌的表演风格形成了
“京油子、卫(天津卫)嘴子”的地方文化共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
国编辑委员会,2008:556);另一方面,民国时期的京津在旗人文化与码
头文化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帮闲”群体与“帮闲”心态,也深刻塑造了相
声“起哄架秧子”的表演形式。 鲁迅( 2005:289)认为帮闲群体及其心态
是“有一件事,是要紧的,大家原也觉得要紧,他就以丑角的身份出现
了,将这件事变为滑稽,或者特别张扬了不关紧要之点,将人们的注意拉
开去”。“帮闲”群体及其“帮闲”心态还深入民国时期京津社会的方方面
面,甚至形成了“‘京派’是官的帮闲”的城市印象(鲁迅,2005:453)。
本文所关注的丧礼相声是一类以丧礼为背景的传统相声, 代表剧
目如《白事会》《福寿全》《夸讲究》《师傅经》《哭当票》等。 虽然华北民间
普遍存在针对高寿逝者的喜丧,但总的来说,丧礼的基本面还是庄严肃
穆悲伤的。 因此,用丧礼找笑料就显得格外刺眼,笑与丧之间巨大的反
差正是用“失常”反思“正常”。 丧礼相声既渲染了处处讲究、程序繁琐
的丧礼, 也用夸张、 扭曲的方式使丧礼变成一场闹剧而引发观众的笑
声。 前者透露出相声所代表的旗人文化对于繁琐礼数的重视,后者则展
现了相声所蕴含的流民文化、 码头文化对于严肃血缘伦理的某种戏谑
心理。 这种在表面文章“礼数”(特别是铺张的仪式)上郑重其事,而在
精神内核“慈孝关系”上戏谑调侃的矛盾行为,正折射了民国时期京津
城市文化与人口流动碰撞下的“帮闲”心态。
基于“反常”的相声有时候也能捅破很多心照不宣的“窗户纸”,把
日常生活中难言、讳言的意思用正话反说的方式加以表达。 譬如,丧礼
相声《师傅经》就点破了京津丧礼讲究的僧道番尼四棚经的悖论之处:
和尚超度亡魂往西方极乐世界,道士请亡魂往东方蓬莱,尼姑请亡魂往
南海观音处,喇嘛请亡魂往北方世界,结果“亡魂一琢磨,干脆,我拜四
方得了”(刘英男,2011d:300-301)。 正因为丧礼是严肃的,参与者都尽
力维护庄严肃穆的氛围,而不是去道破其中的盘根错节、明枪暗箭,因
·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