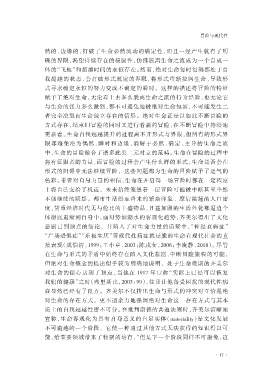Page 24 - 《社会》2022年第4期
P. 24
冒险与现代性
然的、边缘的,打破了生命必然流动的确定性,而且一经产生就有了明
确的界限,渴望持续存在的稳固性,仿佛脱离生命之流成为一个自成一
体的“飞地”和超越时间的永恒存在。然而,绝对生命每时每刻都处于自
我超越的状态,会打破形式既定的界限,将形式重新拉回生命,导致形
式寻求确定永恒的努力变成不确定的瞬时。 这样的描述将冒险的特征
赋予了绝对生命,无论看上去多么脱离生命之流的行为经验,也无论它
与生命的张力多么激烈,都不可避免地被绝对生命包容,不可能发生二
者完全决裂而生命独立存在的情形。 绝对生命正是以如此不断冒险的
方式存在,结束旧冒险的同时又进行着新的冒险,在不断冒险中持续地
更新着。 生命自我超越提升的过程离不开形式与界限,但所有的形式界
限都难免沦为偶然、瞬时和边缘,消解于必然、确定、主导的生命之流
中,生命的冒险融合了诸多此类二元对立的范畴。 生命在冒险的过程中
拥有征服者的力量,而冒险的过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形式,生命是否会在
形式的阻碍中无法继续冒险, 这些问题都为生命的冒险赋予了运气的
色彩。 带着对自身力量的相信,生命在开启每一场冒险时都在一定程度
上将自己交给了机运, 未来始终笼罩着一层冒险可能被中断甚至全然
不能继续的阴影。 都市生活纷至沓来的繁杂印象、 摩肩接踵的人口密
度,货币经济时代无与伦比的丰盛物品、日益加剧的生活外化都逼迫个
体彻底退缩到自身中,面对势如潮水的客观化趋势,齐美尔得出了文化
悲剧已到顶点的结论, 并陷入了对生命力量的质疑中,“神经衰弱症”
“ 广场恐惧症”“乐极生厌”等现代性病症就是脆弱生命在现代社会的直
接表现(成伯清,1999;王小章,2003;陈戎女,2006;李凌静,2018)。 尽管
在生命与形式的矛盾中始终存在陷入文化悲剧、中断冒险旅程的可能,
但绝对生命概念的提出似乎较为明确地说明, 处于生命晚期的齐美尔
对生命的信心达到了顶点,当他在 1917 年宣称“实际上已经可以恢复
我们的健康”之时(弗里斯比,2003:99),往日让他备受困扰的现代性病
症显然已经有了良方。 齐美尔不仅指出生命与形式的冲突对立恰是绝
对生命的存在方式, 更不遗余力地强调绝对生命这一存在方式与其本
质上的自我超越性密不可分。 在批判康德的普遍法则时,齐美尔清晰地
宣称,生命客观化为具有自身意义的自足实体(materiality)是文化发展
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 它使一种通过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知识得以可
能,给重要领域带来了特别的培育,“但是下一个阶段同样不可避免,这
·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