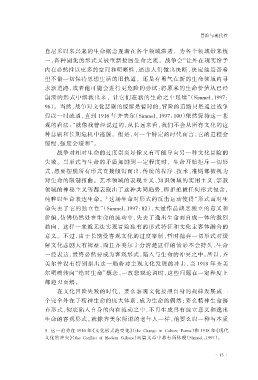Page 20 - 《社会》2022年第4期
P. 20
冒险与现代性
自尼采以来兴起的生命概念逐渐在各个领域渗透, 为各个领域带来统
一,各种固化的形式又被重新拉回生命之流。 战争会“让外在现实给予
内在必然性以更多的空间和明晰性,逼迫人们做出决断,决定他是否希
望不惜一切保持思想生活的旧轨道, 还是有勇气在新的生命领域内寻
求新道路,或者他可能会进行更危险的尝试:将原来的生命价值从已经
崩溃的形式中解救出来, 让它们在新的生命之中延续”( Simmel,1997:
96)。 当然,战争对文化悲剧的缓解是暂时的,冒险的道路只是通过战争
得以一时疏通,直到 1916 年齐美尔(Simmel,1997:100)依然保持这一悲
观的看法:“就像我曾经说过的,从长远来看,我们不会从所有文化的这
种悲剧和长期危机中逃脱。 但是,对一个特定的时代而言,它的进程会
缓慢,强度会缓和”。
战争对相对生命的过度崇尚好像又有可能导向另一种文化冒险的
失败。 当形式与生命的矛盾加剧到一定程度时, 生命开始拒斥一切形
式,想要摆脱所有形式直接倾泻而出,传统的程序、技术、准则都被视为
对生命的限制扭曲。 艺术领域的表现主义、知识领域的实用主义、宗教
领域的神秘主义等都表现出了这种共同趋势,即拒绝被任何形式包含,
纯粹以生命表达生命。 5 这场生命对形式的反击运动使得“形式面对生
命失去了它的独立性”(Simmel,1997:82),大量作品缺乏独立的意义和
价值,仿佛仍然处在生命的流动中,失去了逸出生命而自成一体的激烈
趋向, 这样一来就无法实现冒险独有的形式特征和文化主客体融合的
意义。 不过,由于长期受客观文化的过度宰制,暂时抛弃一切形式对缓
解文化悲剧大有裨益,而且齐美尔十分清楚这样的情形不会持久,生命
一经表达,最终必然要成为客观形式,陷入与生命的冲突之中。所以,齐
美尔并没有特别指出这一趋势对主观文化发展的冲击,当 1918 年齐美
尔明确转向“绝对生命”概念、一改悲观论调时,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都迎刃而解。
在文化冒险失败的时代, 要么客观文化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成一
个完全外在于精神生命的庞大体系,成为生命的偶然;要么精神生命摒
弃形式,彻底陷入自身的内在流动之中,不再生成具有独立意义和逸出
生命的客观形式。 就像齐美尔所说的老年人一样,他要么以一种与本质
5. 这一趋势在 1916 年《文化形式的变化》(the Change in Culture Forms)和 1918 年《现代
文化的冲突》(the Conflict of Modern Culture)两篇文章中都有所体现(Simmel,1997)。
·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