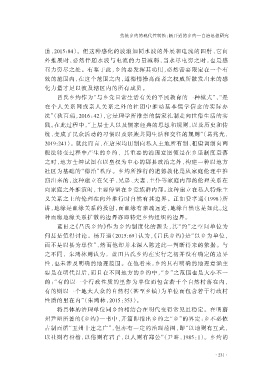Page 238 - 《社会》2022年第4期
P. 238
传统乡约的现代性转换:杨开道的乡约—自治思想研究
道,2015:84)。 但这种感化的波浪如同水波的外展和电流的四射,它向
外推展时,必然伴随水波与电流的力量减弱,当水尽电穷之时,也是感
召力穷尽之处。 有鉴于此,乡约要发挥其功用,必然需要限定在一个有
效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之内,道德情操高尚者之权威所散发出来的感
化力量才足以波及辖区内的所有成员。
吕氏乡约作为“与乡党日常生活有关的平民教育的一种模式”,“是
在个人关系网或亲人关系之外的社团中推动 基 本 儒 学 信 念 的实 际 办
法”(狄百瑞,2016:42),它是理学所推崇的儒家礼制走向世俗生活的实
践。在此过程中,“上层士人以及儒家经典的思想和规则,以及历史和传
统,变成了民众活动的习惯以及宗族共同生活和交往的规则”(葛兆光,
2019:241)。 就此而言,在唐宋均田制向私人土地所有制、租庸调制向两
税法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乡约, 其重要的治理意图便是在乡里制度衰落
之时,地方士绅试图在以皇权为中心的郡县政治之外,构建一种以地方
社区为基础的“德治”秩序。 乡约所推行的道德教化是从家庭伦理中推
演出来的,这种建立在父子、兄弟、夫妻、主仆等家庭内部的伦理关系在
向家庭之外推演时,主要停留在乡党族群内部。 这种建立在私人特殊主
义关系之上的伦理在向外推行时自然有其边界。 正如费孝通(1998)所
讲,地缘是血缘关系的投射,而血缘有亲疏远近,地缘自然也是如此。这
种血缘地缘关系扩散的边界亦即特定乡约组织的边界。
蓝田之《吕氏乡约》作为乡约制度化的源头,其“约”之空间单位为
何甚是值得讨论。 杨开道(2015:69)认为,《吕氏乡约》是“以乡为单位,
而不是以县为单位”,然而他却并未深入陈述此一判断得来的依据。 与
之不同, 朱鸿林则认为, 蓝田吕氏乡约在实行之初并没有确定的边界
性,也未涉及明确的地理范围。 在他看来,乡约具有明确的地理意涵主
要是在明代以后,而且在不同地方的乡约中,“乡”之范围也是大小不一
的:“有的以一个行政性质的里作为单位而包含若干个自然村落在内,
有的则以一个地大人众的自然村(甚至乡镇)为单位而包含若干行政村
性质的里在内”(朱鸿林,2015:353)。
将具体的治理单位同乡约相结合在明代变得常见且稳定。 在明蔚
州尹畊所著的《乡约》一书中,开篇即指出乡约之“乡”的界定:乡不必依
古制而循“五州十连之广”,但亦有一定的治理范围,即“以地则有互武,
以社则有枌榆,以俗则有君子,以人则有郑公”(尹畊,1985:1)。 乡约的
· 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