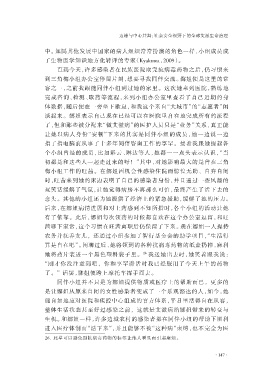Page 154 - 《社会》2022年第3期
P. 154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
中。 如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病人组织常常扮演的角色一样,小组成员成
了生物医学知识地方化转译的专家(Kyakuwa,2009)。
直到今天,许多感染者在民族医院取完抗病毒药物之后,仍习惯来
到三角梅小组办公室停留片刻,想要寻找同伴交流。 娜姐便是这里的常
客之一,之前我跟随同伴小组到过她的家里。 这次她来到医院,熟练地
完成咨询、检测、取药等流程,来到小组办公室里查看了自己近期的身
体数据,随后便在一旁坐下歇息,和我这个来自“大城市”的“志愿者”闲
谈起来。 娜姐表示自己现在已经可以在医院里自在地完成所有的流程
了,但和那些被分配来“做艾滋病”的医护人员只是“业务”关系,真正能
让她以病人身份“安顿”下来的其实是同伴小组的成员,她一边说一边
指了指电脑前从事了十多年同伴咨询工作的享罕。 接着我跟她提起各
个小组曾经的成员,比如彩云、琳达等人,她都一一点头表示认识,“当
初都是和这些人一起走过来的呀! ”其中,对她影响最大的是曾在三角
梅小组工作的旺茜。 在娜姐因机会性感染住院而惊惶无助、 自弃自闭
时,旺茜来到她的床边表明了自己的感染者身份,并且通过一些风趣的
玩笑话缓解了气氛,让她觉得病房不再那么可怕,最终产生了活下去的
念头。 其他的小组还为她提供了经济上的紧急援助,缓解了她的压力。
后来,在娜姐病情进展和对上药感到不知所措时,各个小组的活动让她
有了依靠。 此后,娜姐每次领药的时候都喜欢在这个办公室逗留,和旺
茜聊下家常,这个习惯在旺茜离职后仍保留了下来。 现在娜姐一人操持
农务并抚养女儿, 还通过小组参加了智行基金会的助学项目,“生活得
算是自在吧”。 闲聊过后,她将领到的各种抗病毒药物的纸盒扔掉,麻利
地将药片装进一个黑色塑料袋子里。 26 我送她出去时,她笑着跟我说:
“刚才你没注意到吧, 你和享罕讲话时我已经服用了今天上午的药物
了。 ” 话罢,娜姐便跨上摩托车挥手而去。
同伴小组并不只是为娜姐提供物质或医疗上的帮助而已, 更多的
是让娜姐从原来自闭的女性感染者变成了一个乐观豁达的人,如今,她
能自如地应对医院和疾控中心组成的官方体系,平日里活得自在从容,
整体生活状态甚至好过感染之前, 这就是艾滋病给娜姐带来的转变与
生机。 和娜姐一样,许多边城农村的感染者都在同伴小组的帮助下顺利
进入医疗体制而“活下来”,并且能够不被“这种病”束缚,也不完全为医
26. 此举可以避免因抗病毒药物的标签让他人看见而引起麻烦。
· 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