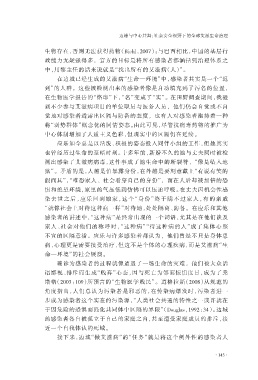Page 150 - 《社会》2022年第3期
P. 150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
生物存在,否则无法获得药物(Biehl,2007);与巴西相比,中国的基层行
政能力无疑强得多, 官方的目标是将所有感染者都涵括到治理体系之
中,用黎主任的话来说就是“找出所有的艾滋病(人)”。
在边城已经生成的艾滋病“生命—环境”中,感染者其实是一个“迟
到”的人群。 这些被检测出来的感染者像是自动填充到了污名的位置,
在生物医学报告的“烙印”下,“名”变成了“实”。 在田野调查期间,我碰
到不少参与艾滋病项目的单位职员与医务人员, 他们仍会自觉或不自
觉地对感染者透露出区隔与防备的态度, 也有人对感染者抱持着一种
将“弱势群体”概念化的同情姿态。由此可见,尽管抗病毒药物的推广为
中心体制增加了人道主义色彩,但现实中的区隔仍在延续。
应乐如今总是以活泼、积极的姿态投入同伴小组的工作,但她其实
也曾经历过生命的至暗时刻。 十多年前,新婚不久的她与丈夫同时被检
测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这件事成了她生命中的断裂符,“像是坠入地
狱”。 矛盾的是,人越是怕暴露身份,在外越是要刻意戴上“有说有笑的
假面具”,“唯恐家人、 社会看穿自己的身份”, 而在人后却被加倍的恐
惧和绝望环绕,家里的气压低到仿佛可以压迫呼吸。 在丈夫因机会性感
染去 世 之 后 ,应 乐 回 到 娘 家 ,这 个“身 份 ”终于 瞒 不 过 家 人 ,有 的 亲 戚
“就像社会上对待这种病一样”对待她,处处隔离、防备。 在应乐和其他
感染者的讲述中,“这种病”是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语,尤其是在他们谈及
家人、社会对他们的称呼时,“这种病”“得这种病的人”成了集体心照
不宣的区隔意指。 应乐与许多感染者都认为, 他们曾经不只是身体患
病,心理更是需要接受治疗,但这不是个体的心理疾病,而是艾滋病“生
命—环境”的社会展演。
确诊为感染者的过程就像遭遇了一场生命的灾难, 他们被大众话
语鄙视、排斥而生成“贱弃”心态,因与死亡为邻而惊惧度日,成为了桑
塔格 (2003:109)所预言的“生物医学贱民”。 道格拉斯(2008)从规范的
角度指出,人们总认为污染者是邪恶的,在传染病爆发时,污染者进一
步成为感染者这个实在的污染源,“人类社会共通的特性之一或许就在
于因危险的恐惧而强化共同体中区隔的界限”(Douglas,1992:34)。 边城
的感染者各自被孤立于自己的家庭之内,甚至遭受家庭成员的排斥,接
近一个自我体认的死域。
接下来,边城“做艾滋病”的“任务”就是将这个例外性的感染者人
·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