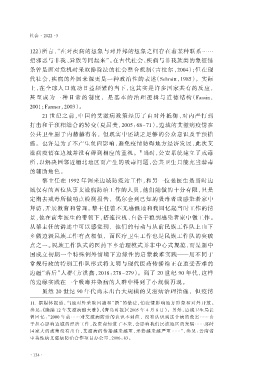Page 141 - 《社会》2022年第3期
P. 141
社会·2022·3
122)所言,“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对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在古代社会,疾病与非我族类的象征链
条曾是面对危机时采取排除法的社会整合机制(吉拉尔,2004);但在现
代社会,疾病的外国来源更是一种政治性的表述( Schmitt,1985)。 实际
上,在全球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这其实是许多国家共有的反应,
甚 至 成 为 一 种 日 常 的 制 度 , 是 基 本 的 治 理 逻 辑 与 道 德 结 构(Fassin,
2001;Farmer,2003)。
21 世纪之前,中国的艾滋病政策经历了由对外抵御、对内严打到
打击和干预相结合的转变(夏国美,2005:68-71)。边城的艾滋病疫情在
公共卫生圈子内赫赫有名, 但现实中还缺乏足够的公众意识及干预措
施。 也许是为了不产生负面影响,避免疫情妨碍地方经济发展,此次艾
滋病疫情在边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 11 当时,公安系统建立了戒毒
所,以解决因邻近缅北地区而产生的吸毒问题,公共卫生只能充当禁毒
的辅助角色。
黎主任在 1992 年调来边城防疫站工作,和另一位老医生是当时边
城仅有的两位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人员,他们能做的十分有限,只是
定期去戒毒所做哨点检测报告, 偶尔会到已知的吸毒者或感染者家中
拜访,开展教育和管理。 黎主任曾不无感慨地和我回忆起当时工作的情
景,他在前辈医生的带领下,搭拖拉机、自备干粮到感染者家中做工作。
从黎主任的讲述中可以感觉到, 他们的行动与从前民族工作队上山下
乡做边疆民族工作有点相似, 而医疗卫生工作也是民族工作队的突破
点之一。 民族工作队式的医药下乡治理模式并非中心式规范,而是新中
国成立初期一个特殊例外情境下边缘性的启蒙救难实践———用不同于
常规行政的特别工作队形式将文明与现代医药传播给正在遭受苦难的
边疆“落后”人群(方洪鑫,2018:278-279)。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这样
的边缘实践在一个吸毒并染病的人群中得到了小规模再现。
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尚未出台大规模的艾滋病治理措施, 但疫情
11. 据媒体报道,当地对外采取回避和“捂”的做法,怕疫情影 响地方 形象和 对外开放 。
参见:《隐瞒 12 年艾滋病酿大难》,《青岛时报》(2005 年 4 月 8 日)。 另外,边城卫生局长
曾回忆:“2000 年前……对艾滋病防治的认识不到位, 没有认识到这个病的危害……由
于担心影响边城的经济工作,投资商知道了不来,会影响我们民族地区的发展……那时
国家大的政策没有出台,艾滋病的传播越来越重,形势越来越严重……”,参见:云南省
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办公室,2006:83。
· 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