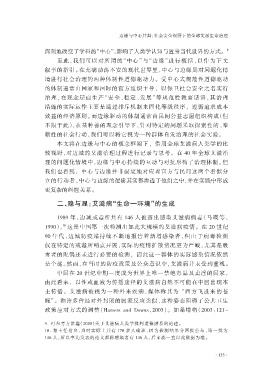Page 140 - 《社会》2022年第3期
P. 140
边缘与中心共舞:社会安全视野下的全球艾滋生命治理
深刻地改变了学科的“中心”,影响了人类学认知与置身当代世界的方式。 9
至此,我们可以对所谓的“中心”与“边缘”进行概括,以作为下文
叙事的指引。 在充满动荡不安的现代世界里,中心与边缘是对问题化情
境进行社会治理的两种体制性道德驱动力。 受中心式规范性道德驱动
的体制通常由国家和国际的官方组织主导, 以保卫社会安全之名实行
治理,在观念层面生产“安全、稳定、发展”等规范性教育话语,其治理
措施的实际运作主要是通过排斥机制来固化等级秩序, 遵循追求成本
效益的经济原则。 而边缘驱动的体制通常由民间公益志愿组织构成(但
不限于此),在某种善的理念引导下,针对特定的问题采取探索性的、奉
献性的社会行动,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群体自发治理的社会实验。
本文将在边缘与中心的概念框架下, 借用全球艾滋病人类学的比
较视野,对边城的艾滋治理过程进行记录与思考。 在 40 年全球艾滋治
理的问题化情境中,边缘与中心持续的互动与对抗形构了治理体制。 但
我们也看到, 中心与边缘并非固定地对应着官方与民间这两个看似分
立的行动者,中心与边缘的逻辑其实都渗透于他们之中,并在实践中形成
更复杂的纠缠关系。
二、隐与显:艾滋病“生命—环境”的生成
1989 年,边城戒毒所共有 146 人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马瑛等,
10
1990), 这是中国第一次检测出如此大规模的艾滋病疫情。 在 20 世纪
90 年代,边城防疫站持续不断地报告着新增感染者,但由于病毒检测
仅在特定的戒毒所哨点开展,实际的疫情扩散情况更为严峻,尤其是吸
毒者的配偶还未进行必要的检测, 因此这一群体的实际感染情况依然
是个谜。然而,在当时的防疫政策及公众意识中,艾滋病并未受到重视。
中国在 20 世纪中期一度成为世界上唯一禁绝毒品及卖淫的国家,
由此看来, 以性或血液为传播途径的艾滋病自然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本
土传播。 艾滋病被视为一种外来疾病,媒体称其为“西方飞进来的苍
蝇”。 和许多曾经对外封闭的国家反应类似,这种姿态阻碍了公共卫生
政策应对方式的调整(Hamers and Downs,2003)。 如桑塔格(2003:121-
9. 可参考方洪鑫(2020)关于艾滋病人类学批判道德谱系的论述。
10. 黎主任指 出,当时 实际上 共有 170 多 人确诊 ,因 为 检 测 结果 分 两 批 公 布,第 一 批为
146 人,所以率先发表的论文都称感染者有 146 人,后来就一直以此数据为准。
·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