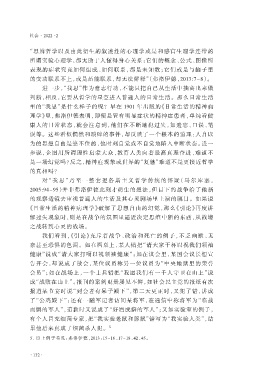Page 139 - 《社会》2022年第2期
P. 139
社会·2022·2
“思辨哲学以及由此衍生的叙述性的心理学或是和感官生理学连带的
所谓实验心理学,都无助于人懂得身心关系;它们的概念、公式、图像所
表现的症状究竟如何组成、如何联系,都是未知数;它们或是与脑子里
的变动联系不上,或是虽能联系,却无法解释”(弗洛伊德,2013:7-8)。
进一步,“我思”作为意志行动,不能只把自己从生活中抽离出来做
判断,相反,它要从哲学的星空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那么日常生活
里的“我思”是什么样子的呢? 早在 1901 年出版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
理学》里,弗洛伊德表明,即便悬置有明显症状的精神症患者,单纯看健
康人的日常状态,就会注意到,他们在不断地犯过失,如遗忘、口误、笔
误等。 这些看似偶然和琐碎的事件,却反映了一个根本的道理:人自以
为的思想自由是靠不住的,他时刻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中断状态。 进一
步说,企图用所谓理性启蒙大众,教育人类向着最高真理奋进,难道不
是一场幻觉吗? 反之,精神症现象或世界的“复魅”难道不是更接近哲学
的真相吗?
对“我 思 ” 乃 至 一 整 套 逻 各 斯 主 义 哲 学 传 统 的 怀 疑(马 尔 库 塞 ,
2005:94-95)并非弗洛伊德此刻才萌生的想法,但目下的战争给了他新
的观察透镜去审视普通人的生活及其心灵剧场里上演的剧目。 如果说
《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破解了思想自由的幻觉,那么《引论》再度讲
解过失现象时,则是在战争的氛围里逼近决定思维中断的东西,从战壕
之战转到心灵的战场。
我们看到,《 引论》充斥着战争、政治和死亡的例子,不乏幽默、无
奈甚至恐惧的色调。 如在酒桌上,某人错把“请大家干杯以祝我们领袖
健康”说成“请大家打嗝以祝领袖健康”;如在议会里,某国会议长想宣
告开会,却说成了散会,某位议员称另一位议员为“中央地狱里的荣誉
会员”;如在战场上,一个士兵错把“我愿我们有一千人守卫在山上”说
成 “战败在山上”。 报刊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如社会民主党的报纸有次
报道某节宴时说“到会者有呆子殿下”,第二天更正时,又犯了错,讲成
了“公鸡殿下”;还有一随军记者访问某将军,在通信中称将军为“临战
而惧的军人”,道歉时又说成了“好酒成癖的军人”;又如实验室的例子,
有个人冒充细菌专家,把“我实验老鼠和豚鼠”错写为“我实验人类”,结
果他后来真成了细菌杀人犯。 5
5. 以上例子参见:弗洛伊德,2013:15-16、17-18、42、45。
· 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