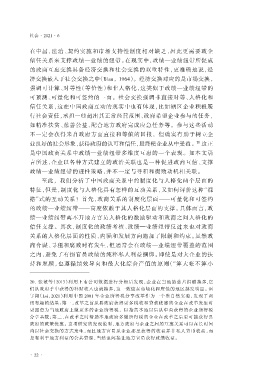Page 29 - 《社会》2021年第6期
P. 29
社会·2021·6
在中国,法治、契约实施和市场支持性制度相对缺乏,因此更需要政企
信任关系来支撑政绩—业绩的纽带。 在现实中,政绩—业绩纽带所促成
的政商互惠交换具备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双重特性,更准确地说,经
济交换嵌入于社会交换之中( Blau, 1964)。 经济交换对应的是市场交换,
强调可计算、对等性(等价性)和非人格化,这类似于政绩—业绩纽带的
可预测、可量化和可签约的一面。 社会交换强调非直接对等、人格化和
信任关系,这在中国政商互动的现实中也有体现,比如辖区企业积极履
行社会责任,承担一些超出其正常经营范围、政府希望企业参与的任务,
如精准扶贫、慈善公益、配合地方政府完成应急任务等。 参与这些活动
不一定会获得来自政府方面直接和等值的回报, 但确实有助于树立企
业良好的社会形象,获得政府的认可和信任,最终使企业从中受益。 20 这正
是中国政商关系中政绩—业绩纽带多维度互惠的一个表现。 如本文引
言所述,企业以各种方式建立的政治关联也是一种促进政商互信、支撑
政绩—业绩纽带的理性策略,并不一定与寻租和腐败动机相关联。
至此, 我们分析了中国政商关系中的制度化与人格化两个层面的
特征,但是,制度化与人格化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又如何评价这种“混
搭”式的互动关系? 首先,政商关系的制度化层面———可量化和可签约
—
的政绩—业绩纽带——高度依赖于其人格化层面的支撑。 具体而言,政
绩—业绩纽带离不开地方官员人格化的激励驱动和政商之间人格化的
信任支撑。 其次,制度化的政绩考核、政绩—业绩纽带反过来也对政商
关系的人格化层面的性质、内涵和发展方向施加了限制和约束。 虽然政
商合谋、寻租和腐败时有发生,但通常会在政绩—业绩纽带覆盖的范围
之内,避免了有损官员政绩的纯粹私人利益捆绑。 即使是对大企业的扶
持和照顾,也遵循绩效导向和最大化综合产值的原则(“算大帐不算小
20. 张敏等(2013)利用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企业在当地的慈善捐赠越多,它
们从政府手中获得的补贴收入也就越多,这一效应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越发明显。 雷
宇翔( Lei,2021)利用中国 2001 年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发现了两
组有趣的结果:第一,改革之前从县政府获得更多税收和贷款优惠的企业在改革发生时
更愿意为当地政府上缴更多的企业所得税, 以抬高本地以后从中央获得的企业所得税
分享基数;第二,在改革之时帮助本地政府多缴所得税的企业在改革之后更可能获得县
政府的政策优惠。 这项研究的发现说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互惠关系可以在长时间
内以社会交换的方式发生,而且地方官员从企业那里获得的收益并非私人货币收益,而
是有利于地方利益的公共资源,当然也间接让地方官员获得政绩收益。
·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