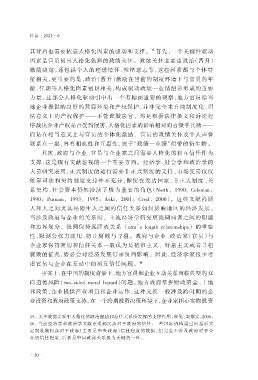Page 27 - 《社会》2021年第6期
P. 27
社会·2021·6
其背后也需要依靠人格化因素的驱动和支撑。 15 首先,一个关键性驱动
因素是官员极具人格化色彩的政绩关怀。 政绩关怀主要由政治(晋升)
激励决定,还包括个人的理想情怀、性格意志等,这些因素都与个体特
征相关,更重要的是,政治(晋升)激励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与官员的年
龄、任期等人格化因素密切相关,构成驱动政绩—业绩纽带形成的重要
力量。 这部分人格化驱动引申出一个有趣而重要的观察:地方官员给当
地企业提供的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产权保护,并非完全来自纯制度化、司
—
法意义上的产权保护——不管谁做法官, 均是根据法律条文和诉讼程
—
序裁决企业产权是否受到侵害,人格化因素的影响相对而言微乎其微——
而是在相当意义上与官员的个体化激励、 官员的政绩关怀及个人声誉
联系在一起,具有相机性和互惠性,属于“政绩—业绩”纽带的衍生物。
其次,政府与企业、官员与企业家之间需要人格化的相互信任作为
支撑,这是现有文献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
大量研究表明,正式制度的运行需要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市场交易仅仅
依靠司法和契约制度支持并不充分,即使在发达国家,非正式制度、关
系契约、社会资本仍然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North, 1990; Coleman,
1990; Putnam, 1993, 1995; Aoki, 2001; Greif, 2006)。 这些文献强调
人和人之间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如何影响地区的经济发展。
当涉及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时, 主流经济学研究更强调两者之间的职能
和边界划分, 强调保持远距离关系 (arm’s length relationships) 的重要
性,限制公权力滥用,防止腐败与寻租。 政府与企业、政治家(官员)与
企业家保持密切和信任关系一般认为是裙带主义、 特惠主义或者寻租
腐败的征兆,势必会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经济学家很少考
虑官员与企业在互动中的相互信任问题。 16
事实上,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地方官员和企业互动关系面临典型的双
向道德风险(two鄄sided moral hazard)问题。 地方政府掌握财政资金、土地
和政策,企业提供产业项目和企业运作,这种交换一般涉及跨时期的企
业投资和政府政策支持。在一个跨期投资决策环境下,企业家担心实物投资
15. 关于政商关系中人格化的政治激励和信任关系所发挥的支撑作用,参见:周黎安,2008。
16. 当前经济学和政治学文献更强调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一些国际机构通过问卷形式
定期收集民众对于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数据,但完全不涉及政府对于企
业的信任程度,后者是中国政商关系极为关键的一环。
· 20 ·